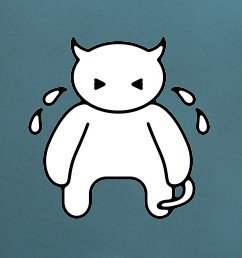坐上12个乘客的小飞机,我们朝森林的一个小点飞行。下面是一望无际的森林,透着马奎斯小说的阴森感,好像满满的都是诡异的故事。我鸟瞰森林,设想坠机之后的可能性,被脑海的画面吓了一跳,而又感觉很刺激。
坐上12个乘客的小飞机,我们朝森林的一个小点飞行。下面是一望无际的森林,透着马奎斯小说的阴森感,好像满满的都是诡异的故事。我鸟瞰森林,设想坠机之后的可能性,被脑海的画面吓了一跳,而又感觉很刺激。飞行的目的地是姆鲁国家公园,在砂拉越州美里的一处森林。那是我见过的最原始的原始森林,原始到了叫人不停思索一旦迷失该怎么办的地步。从国家公园总部出发到营地,需要乘船和走八公里的路,八公里的路走完后,就是背山面水的世外桃源。
 营地旁边有一座吊桥,桥下是水凉如冰的河流,根据桥头告示牌的说法,桥通去一个猎头族的部落。我们没有去找猎头族,倒是去看了美国前总统林肯的侧面头像。呼吸着蝙蝠粪便的味道走在宽广的鹿洞里,刚被慵懒的钟乳石摄去了三魂,附身洞壁的林肯就跑了出来夺走剩余的七魄。
营地旁边有一座吊桥,桥下是水凉如冰的河流,根据桥头告示牌的说法,桥通去一个猎头族的部落。我们没有去找猎头族,倒是去看了美国前总统林肯的侧面头像。呼吸着蝙蝠粪便的味道走在宽广的鹿洞里,刚被慵懒的钟乳石摄去了三魂,附身洞壁的林肯就跑了出来夺走剩余的七魄。我站在漆黑的洞内,仰望天然构成的林肯侧面头像,和飞成曲线成群归巢的蝙蝠,想了一些宇宙和人的事。那一刻,时间停摆,流过的,只有感动。
烦恼时,想起远处有一座相识的森林,以流传了亿万年的规律,自顾自地生息着,烦恼似乎就微不足道了。一生的时间,尚不及一毫米的钟乳石,烦恼在这宇宙间,算得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