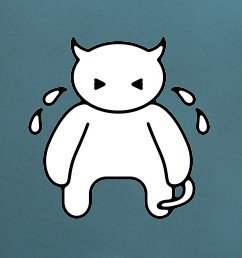离开吧,离开吧,众人一直在我耳边念叨。我在荆棘中跋涉,让脚步声盖过咒语般的念叨声,径直往前走。偶一回头,景观尽是众人的唏嘘与不舍。有那么一刻,我瞥见他们手中紧握的线头......
离开吧,离开吧,众人一直在我耳边念叨。我在荆棘中跋涉,让脚步声盖过咒语般的念叨声,径直往前走。偶一回头,景观尽是众人的唏嘘与不舍。有那么一刻,我瞥见他们手中紧握的线头...... 对我的家人来说,我当上记者,是家里一个不小的悲剧。我是那种小时了了的物种,从小就在众人的赞叹声中长大。纵然长大后应了“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预言,众人的印象还是停留在我的“辉煌时代”。大家以为,我长大后会成为医生、律师,再不然就科学家、教授,怎么也想不到我会“不济”到会去当记者跑新闻。
决定闯关时,养育我的伯伯问了又问:“当记者好吗?”爸爸不停说着别人家的故事,说别人的女儿如何如何“本事”。左邻右舍和亲戚听了,也都说:“世道不好,就先做做,骑牛找马吧。”一阵阵心碎的声音,几乎撕裂我的记者梦。
望女成凤的梦想破灭以后,伯伯给我的,不是叹息声和埋怨声,而是掌声和鼓励。《东方日报》是我的第一个雇主,家乡无人代理《东方日报》,伯伯于是逮住每周我文章刊出的那一天搭巴士到半小时外的小镇买一份《东方日报》,珍藏我的作品,朋友到访时骄傲地展示一番。
我如斯感动,也如斯惭愧。既然文章见报让家人引以为豪,为何这选择始终无法让他们释怀?要到何时,我们才终于建立起新闻从业员的声誉地位,让爱我们的人不必产生这种“自豪而又惋惜”的矛盾心理?
人是自私的,人们知道新闻担当上传下达的重任,该由文笔、思考能力、批判能力俱佳的人撰写,可是当符合资格的人恰恰是他们的亲人,他们就说什么也不愿意让他投身新闻界了。
谁不想自己所爱的人好?新闻界乌烟瘴气,记者前(钱)途茫茫,因此,眼见自己所爱的人投身其中,“想要拉他一把”的念头,自自然然地产生。局内人身处荆棘,背后尚且还有众人热情的召唤,该当如何奋力向前?
纵然我是背负抱负而来的,有时竟也迷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