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们不介意吧,就算你们介意我也没有办法,身体辛苦了一整天,我要让它放松一下。”瑞典安娣说。
我和另一个女的客气地说声“没关系”,这个受刑一天的瑞典安娣就在我们面前老实不客气地脱去身上的衣服。我看了一眼她赤裸的上身,眼睛移回书页上,没去进一步见证她是否一丝不挂。
在瑞典的经济旅舍醒来的那个早上,眼睛在共用的洗澡间里遇到另两个瑞典裸女。她们在没有门的浴室里一边洗澡一边谈话,像两只未长羽毛的小鸟,啾啾叫着在夏天的雨中淋浴。眼睛跟裸体打招呼时禁不住失望:在陌生人面前裸体,不过就这么一回事。
眼镜期待着一些类似“震撼”或“震惊”的感觉,可是没有。裸体在于瑞典女人,自然得就像我们冲凉习惯关门一样,让我这种假扮君子的荒蛮人不得不相信,裸体的画面纯粹是自然界的构图。
臃肿的瑞典安娣睡在我的头上,鼾声此起彼落。我和她和一名在芬兰念大学的瑞典女生挤在一个小船舱里,共度一个无惊无险的晚上(算来惊险事也还有一桩,凌晨不知何时何刻安娣的一袋不知什么东西从天而降,砸醒了睡在她床下的我)。
睡前收拾行李时我摸出了一粒让我相当为难的橙。这粒橙跟着我从赫尔辛基飘洋过海16小时来到瑞典,又跟着我回到航向赫尔辛基的海路上。我问安娣是不是要让橙跟她去,她说好好好,开车去俄罗斯的路上正好吃它。可是第二天醒来临走前,她却把它忘在小桌子上。
这粒橙是在酒店的自助早餐中“偷”的。想着在早餐过后吃它,可是早餐过后却一直找不到机会吃它。陪我游玩了一趟瑞典之后,最后它又回到了酒店里。剖开它的外衣吃起它的时候,它成了至今我吃过的最香甜可口的一粒橙。
回来以后我一直在翻找记忆,寻来觅去,只找到了三幅裸体,和一粒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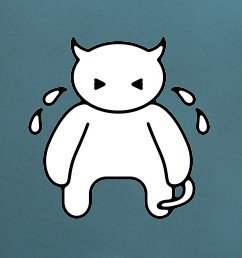
2 comments:
你在斯德哥尔摩睡在船舱,那我们可能凑巧的住进同一艘旅馆了。
华哥,这篇文章一定是写得太糊涂了,难怪你会以为我住的是那船旅馆。不是啦,不是啦,文章的场景有两个,一个是Vikingline船舱,另一个有两只裸体小鸟的是Stockholm的一家经济旅舍。我穿插着写。
你说的船旅馆是不是红色的那艘泊靠近Vikingline码头的船旅馆?带我去玩的读者指过给我看。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