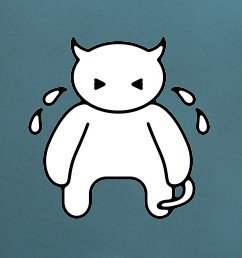他站在一托托的鸡蛋前,看了又看,看了又看。他问我多少钱一粒,我说我不是售货员,你要问里面。柜台堆满了我的食物,这两个星期我都在做囤货的事情,尽能力为可能高涨的物价做好准备。我随手取了一排Omega Plus鸡蛋,回到收银处付钱。鸡蛋多少钱?他问。一粒30仙,收银员说。他又回到一托托的鸡蛋面前,看了又看,看了又看。最后他捧着四粒鸡蛋回到收银处。我正在为我选好的饼干、韩国面、零食、罐头,还有一排十粒的鸡蛋付款。
他用他粗糙的双手,庄重地捧着四粒鸡蛋,像捧着四粒足可让全家温饱的金蛋。我突然好想藏好我的十粒Omega Plus鸡蛋,我怕。我怕我让他酸了他的鼻子。而我,我已经酸了我的鼻子。
物价飞涨之前,我还有囤货的能力,可是这名印度老兄呢?买四粒鸡蛋尚且让他如此庄重其事,每天家里柴米油盐的事,他真能应付吗?他购买鸡蛋之前左思右忖的,是每个家人该分得一粒鸡蛋的几分之几?还是这一餐吃了四粒鸡蛋之后,下一餐该吃些什么?我怕,因为我知道,1元20仙在很多月入只有几百元的厂工、园丘工人家庭来说,确确实实是一个沉重的数字。我怕,因为燃油、物价高涨之前,他们已是生活拮据了,燃油和物价高涨之后,他们该怎么活下去?
我可以理解,攫夺案为何接踵而来、爆劫案为何时有所闻。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能让他怎么样?奶粉要钱、上学要钱、食物要钱、生病要钱,以前还说杂货店老板可以让你记帐,现在除了阿窿,谁让你记帐?在偷、抢、死面前,他该怎么选择?
为了环境、为了下一代,我愿意承担更多的油钱。面对通货膨胀,可能我只需要从鸡腿饭转去吃鸡胸饭、从四样菜转吃两样菜,可是在真正贫穷的人士而言,他们面对的可是攸关生死存亡问题的断粮危机,坐官车、进出大酒店的高官,你们食民俸禄,该担民之忧!
政府在调升油价之前,还需考量到贫穷人士的需要,提出一个周详的方案度过通膨危机,譬如制定最低薪金制、拟定发放救济金制度。至于说把燃油津贴转向津贴食物,我希望真的有实际效用,别又在两年后告诉我,津贴缩水了,所以我们什么也没做到。
我相信,如果我国的公共交通发达,很多人愿意弃车改乘公共交通工具。几十年来,政府为了我国的国产车政策,投注巨额发展公路和大道,忽略了公共交通系统的发展,现在一夜之间调升油价高达40至63%,呼吁人民“改变生活方式”,怎么可能?
你要我与政府共赴时艰,也请让我看到你是认认真真地领导人民度过这个艰难时期,而非让我感觉自己坐困愁城动弹不得。因此,如果你是负责任、爱民的政府,请你认真规划我国的公共交通系统以及拟定兼顾环保与人民需要的能源政策。
朋友告诉我,他只等着安华上台,宣布降油价。我只想告诉安华,降油价只能解人民一时之困,我国的燃油和世界燃油总有耗尽的时候,你这个宣布背后是否有完善的机制支撑?如果没有,我只能说,如果你上台,我们不过是送走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迎来另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
Saturday, June 28, 2008
Friday, June 27, 2008
恶魔,你只差没吃掉我的手
恶魔咬噬着我,一口接一口,咀嚼的声音造成了我的精神困扰。耳朵只能靠睡眠闭上。我只能期待睡眠。生活它已经没有晨昏之分,我活在清晨我活在炎午我活在冷夜,睡眠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到来。
我说,现在的我只是得过且过而已。我说。想象你的耳朵就在我的嘴边。麻木地工作到凌晨第二天醒来再麻木地工作一天、每一次休完周假回到公司就在幻想周五、超过一星期的事都不敢想,就是得过且过。那样周而复始地活着,我以为自己已经丧失了时间观念,跑出时间的框框一看,发现原来自己就活在时间里,那么仓惶那么狼狈那么孤单那么虚无。我没有忧伤,我只是空空的,像一只有气没力的气球,在时间里玩升降的游戏。我真的没有忧伤,我只是在无意中白了我的头发。
恶魔还在咀嚼着我。我该睡了。
我说,现在的我只是得过且过而已。我说。想象你的耳朵就在我的嘴边。麻木地工作到凌晨第二天醒来再麻木地工作一天、每一次休完周假回到公司就在幻想周五、超过一星期的事都不敢想,就是得过且过。那样周而复始地活着,我以为自己已经丧失了时间观念,跑出时间的框框一看,发现原来自己就活在时间里,那么仓惶那么狼狈那么孤单那么虚无。我没有忧伤,我只是空空的,像一只有气没力的气球,在时间里玩升降的游戏。我真的没有忧伤,我只是在无意中白了我的头发。
恶魔还在咀嚼着我。我该睡了。
Sunday, June 22, 2008
Friday, June 06, 2008
从这一次到下一次
又发生了好多事。首先是“媒体自由行”。我原是兴致勃勃准备去的,同事们也是,都说好了一起穿《独立新闻在线》的警察t-shirt一同走的,可是最后竟闹出“取消步行”的事,理由还是“没有集会准证”、“担心阻碍交通”等,好没来由的。
心中的闷气一泻千里。我说你们筹办这么重大的活动竟没有周详计划,我说发动记者上街要有明确的目标,我说如果要考量NUJ的想法就该早早考量,别到最后一分钟才说“因为NUJ......,所以......”。我说我不去了。
我真的不去了。
我知道是情绪反应,可要我在一天时间内即刻调适情绪,接受“步行没有取消,只是沟通失误”的解释,第二天又开开心心地去摇旗子,我还真的没法办到。只是从照片中看到老羊去了、郑丁贤去了、Wong Chun Wai去了,心中还是很开心的。
沟通失误、资料失准、目标模糊,回到来还是筹备仓促的问题。律师公会主席Ambiga说,“lawyers seldom walk”,lawyers seldom walk,可记者可是never walked呀(有没有人有印象记者曾上街争取新闻自由?),要号召从来没有凝聚力的各媒体记者为媒体自由而行,理应慎重一点、计划周详一点。
可是,那已是过去了。筹备活动并非易事,社会运动只有少数人在动,其他人都在坐享其成(包括我)。筹备出状况了,筹备的人被骂到臭头,尽管他们是一番好意一卷热肠一心做好事。我想,我原谅了(其实没有资格说原谅),我一边惭愧自己没有付出,一边原谅了。
很多代人的努力,可能在这一代开花结果。争取废除新闻恶法,我们当新闻从业员的,该是责无旁贷的。这个过程需要很多人的参与,就算我们没有时间投身筹备活动,也该在能力所及配合和鼓励推动巨轮的人。
我期待下一次。
如果还有下次,我希望我有机会成为人群的一分子,还希望报社总总们可以跟随郑丁贤和Wong Chun Wai的步伐,用脚走出改善新闻环境的决心。
心中的闷气一泻千里。我说你们筹办这么重大的活动竟没有周详计划,我说发动记者上街要有明确的目标,我说如果要考量NUJ的想法就该早早考量,别到最后一分钟才说“因为NUJ......,所以......”。我说我不去了。
我真的不去了。
我知道是情绪反应,可要我在一天时间内即刻调适情绪,接受“步行没有取消,只是沟通失误”的解释,第二天又开开心心地去摇旗子,我还真的没法办到。只是从照片中看到老羊去了、郑丁贤去了、Wong Chun Wai去了,心中还是很开心的。
沟通失误、资料失准、目标模糊,回到来还是筹备仓促的问题。律师公会主席Ambiga说,“lawyers seldom walk”,lawyers seldom walk,可记者可是never walked呀(有没有人有印象记者曾上街争取新闻自由?),要号召从来没有凝聚力的各媒体记者为媒体自由而行,理应慎重一点、计划周详一点。
可是,那已是过去了。筹备活动并非易事,社会运动只有少数人在动,其他人都在坐享其成(包括我)。筹备出状况了,筹备的人被骂到臭头,尽管他们是一番好意一卷热肠一心做好事。我想,我原谅了(其实没有资格说原谅),我一边惭愧自己没有付出,一边原谅了。
很多代人的努力,可能在这一代开花结果。争取废除新闻恶法,我们当新闻从业员的,该是责无旁贷的。这个过程需要很多人的参与,就算我们没有时间投身筹备活动,也该在能力所及配合和鼓励推动巨轮的人。
我期待下一次。
如果还有下次,我希望我有机会成为人群的一分子,还希望报社总总们可以跟随郑丁贤和Wong Chun Wai的步伐,用脚走出改善新闻环境的决心。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