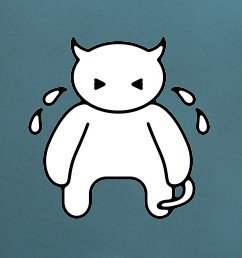伯伯告诉我,村子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果然是一件大事。有人要来我们的华小旁建一所淡小,这是好事。可是,他们要占去草场的一半面积建食堂,这是大事。
如果你到过地里望我的家乡,你就知道那是一个多么好的草场。
从吉隆坡到地里望,要走三十分钟的弯路,弯路之所以弯,皆因它随河型而建,两旁都是橡胶园、榴莲园,偶尔有几个“园口”(村里人都这么唤它,该是“园丘的路口”的简称)。要到地里望时,先是见到一丛茂密的竹丛。竹子长得老高,尖端都弯垂下来,像是鞠躬迎宾的样子,我想该管它们叫迎宾竹。
过了迎宾竹,转了个弯,右边就是中华义山,山以恰到好处的斜度上斜,满山的坟墓都一目了然,抬头望去总有一种“死人呀在这村里也有个位置”的感觉。
坟山下面是关帝庙,坟山就归这庙的负责人管的。开车拐过义山前的弯路,眼前豁然开朗。你见到了我们的草场。草场的绿是这个村的生命力所在,赶路的人经过这里,都要因这草场的绿而精神一振。草场的草生得非常好,密密的没有光秃的地方。小学时我们就在这个草场上赤脚奔跑,运动会要来时学校的鼓笛乐队、红星月队、童子军傍晚总要到草场上操练和彩排。如果你留心看,草场两端都有个门栏,你就知道草场是个足球场。以前村里的警员们和马来村人,傍晚都组队到这里踢足球。
每年的运动会是草场最意气风发时候。运动会前校工会把草场的草都用割草机割一遍,然后用“油屎”在草皮上团团转一圈、两圈、三圈……重新画上足有400米长的田径赛跑跑道。运动会那天小学生们都因这焕然一新的草场而兴致高昂,每双小鞋子内似乎都藏着一双按耐不住要脱了鞋在草场上奔跑的小脚。这片草长得那么良善,没有人愿意对它起什么疑心。赛跑时孩子们都全无戒心地赤足在上面冲刺,家长们也都非常放心地让自己的孩子赤足在草皮上进行各种运动项目。
这草场的草长得这么好是有原因的。伯伯告诉我,草场的草原来生的非常糟糕,有一处没一处的,村子于是派出一个有罗里的村人,到一小时车程外的文冬吉打里新村载回牛粪,这样来回十多二十趟,到牛粪把草场都铺满,草才终于长好。
这草生了足有47年,草场也伴了村人47年,它是地里望华小、地里望新村的一部分,也是每个曾在这儿求学、居住的人心中的一部分。现在地里望华小已经没有鼓笛乐队,听说乐队制服也已经被变卖了,可是每次看到这座草场,我总要想起小学时我穿着鼓笛乐队的制服在草场上击鼓操步的画面。我以为,乐队不是永恒的,草场是,可是草场也竟是要消失的。
伯伯一再强调,这草场每个村人都有一份。60年代的村子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村里人只能打篮球、踢足球、打羽球。于是村人发起凑钱建一座足球场。热心的村人挨家挨户凑钱,可那时村人都穷,每家每户只能一两元地捐。为着筹募更多的钱,村人办了一场慈善义演,请电台的DJ登台,奈何筹到的钱依然未足数。发起人之一的阿尖后来捐出600大元,草场才得以开建。600元在当时是很大了,伯伯说。
阿尖早已去世了。因着建着草场的功劳,他还留在村人的心上。这次草场有难,村人都想起阿尖。阿尖是村里第一个读书人,他在时村人都托他读马来文英文公函。如果阿尖还在,他肯定要拼了老命上书的。
草场没了一半是件大事,没有人可以想象它缺了一半的样子,更没有人可以想象它上面立了座食堂的样子。村子的土地多的是,何不征用草场边的其它土地,还留着草场让华小与淡小的孩子共乐?我同意在村中建一所淡小,让园丘的印度人孩子有机会接受母语教育,可是一所估计学生只有60人的淡小,何须征用那么大一片土地建一座食堂?教育部或州教育局是怎么批的图册?
他们都说地里望是个美丽的村子。这美并非凭空而来的,这美是村人一点一点的心血累计。而美的消失总是从局部的破坏开始。如果现在我们不以为意,数十年后游子回乡,就再也认不得来处了。
Saturday, April 25, 2009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