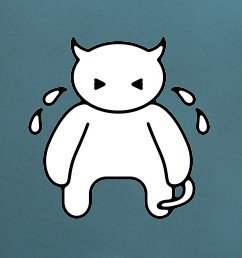最近一直没有睡好,就算是睡了,奇形怪状的梦总是来纷扰。
昨晚,某媒体人开着直升机,把Tun Abdul Samad building的一处吊起,运到某处当讲座会的背景装置。我站在一隅见识别人的能耐,暗自着慌。我知道自己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做那么具震撼力的背景装置,在我的讲座会会场,我只能堪堪把东西摆正而已。
另一个晚上,我们上了巴士,要到砂拉越采访某党大会。我们坐在巴士尾端,斜后座一前一后坐着两个大人物,两人都神情凝重。巴士向荒凉处驶去,我们在座位上嘻哈谈笑,偶尔回头瞄视,两个大人物还是神色凝重。
后来,我们几个走到了巴士的挡风镜前。一具吊在半空中的尸体向我们冲来。我吓呆了。司机没有煞车,径直向尸体冲去。没有碰撞声,没有溅血场面,司机告诉我,那是幻象,某党试图阻挠巴士前进而设置的幻象。
幻象一直向我们袭来,吊在半空的尸体、躺在地面上痛苦挣扎的人们。每一次尸体迎面撞来,我的心就猛烈跳动一次,如此惊吓着前行,良久,我才知道我可以回到座位上闭上眼睛。(后方的两个大人物,似乎由始至终都镇静地闭上眼睛。)
巴士向更荒凉处驶去,四周是森林,在阳光照射下,景物苍白无血色,巴士孤独地走在颠簸的黄沙路上。幻象终于消失了。司机解释道,这里荒凉得就连坏人要设置幻象亦无从设置。我想那关系到线路问题,在路上设置幻象需要无线线路,没有线路,幻象自然就无从设置了。
我们战胜了幻象,但是我不知道最后我们有没有去到砂拉越,我想应该没有,在梦里的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坐巴士是没法去到砂拉越的。
醒来以后,我回到了一样充满幻象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美好的想象吹弹可破,我用仅有的力气抵挡恐怖的幻象,心惊胆战,精疲力竭。我只能想象,自己有一颗强壮的心,在我学会闭上眼睛之前。
Monday, March 15, 2010
Sunday, March 07, 2010
我的狮子头
蓬蓬的头发透出油烟味,好像头发里面一直有个人在炒菜,如果可以我真想把头发取下来,出门的时候才又戴回去。新年前我去做了卷发,我的头发很茂盛,做出来蓬蓬的,像狮子,才知道当狮子很不容易。
我小时候一直留着椰壳头,但小学时经常欺负我的男同学叫我“狮子头”,我总是很生气回敬他“大番薯”。其实小时候我从来没像过狮子,会有“狮子头”的称号只因我的名字有个“思”字,真是莫名其妙。由于这花名来的太莫名其妙,当时的我觉得委屈非常,经常因而跟男同学推桌子大打出手。小时候的我总是跟男生打架,好像我和他们有着什么有深仇大恨。
后来有人授招说,当别人唤你花名的时候你莫理他,他就自讨没趣了,果然强忍了一段时间,“狮子头”终于离我而去,只是狮子掉头离开之后,我变成了大水牛。你听男生给我的称号就知道,我从来不是男生会喜欢的女生。在人和人的圈子里我总是横冲直撞,既像狮子,又像牛。
如此莽莽撞撞过了十余年,身上的尖角都已经撞落、磨平,就算我摆出个狮子头来,认得我的人故人想必亦没几个。如果当年的小男生还来唤我“狮子头”,我想我会笑着向他狂奔而去,像被困在城市的狮子回到他离开已久的森林。
我小时候一直留着椰壳头,但小学时经常欺负我的男同学叫我“狮子头”,我总是很生气回敬他“大番薯”。其实小时候我从来没像过狮子,会有“狮子头”的称号只因我的名字有个“思”字,真是莫名其妙。由于这花名来的太莫名其妙,当时的我觉得委屈非常,经常因而跟男同学推桌子大打出手。小时候的我总是跟男生打架,好像我和他们有着什么有深仇大恨。
后来有人授招说,当别人唤你花名的时候你莫理他,他就自讨没趣了,果然强忍了一段时间,“狮子头”终于离我而去,只是狮子掉头离开之后,我变成了大水牛。你听男生给我的称号就知道,我从来不是男生会喜欢的女生。在人和人的圈子里我总是横冲直撞,既像狮子,又像牛。
如此莽莽撞撞过了十余年,身上的尖角都已经撞落、磨平,就算我摆出个狮子头来,认得我的人故人想必亦没几个。如果当年的小男生还来唤我“狮子头”,我想我会笑着向他狂奔而去,像被困在城市的狮子回到他离开已久的森林。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