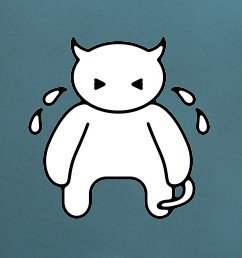我回到了彭亨的家中。这是个阳光喜欢亲近的地方,午间总是热的,现在就连晚间也热了。这里最近闹瘟疫,基孔肯雅,以前闻所未闻的一种蚊症,得病的人脚肿、脸红、骨痛、头昏。伯得了,康复中。
伯伯跟他的书画老友最近在学写诗。我最近几次回家,伯伯总兴致高昂地捧诗与我看。
今天村里死了人,晚上伯伯和爸爸到丧家去。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看配有蔡志忠漫画的唐诗。在风扇和床的怂恿下,竟也即兴乱涂一番。
题:炎夜读李
(一)
坐卧风扇前
炎气心中生
手捧李白书
心向水云间
(二)
甲长未及修
蓬发直披肩*
研书尘寸厚
卧吟李白诗
* 原句:发颠面如土
(三)
风扇自吹夜自凉
闭窗犹传喃无音
心随李庄醉山水
深斎无酒脸自红
题:病村
甲杯瘟疫生
阿伯复得病
蚊虫(*)灭不尽
余恐带疫身
* 我想打“虫内”一字。此字怎念?
Sunday, August 31, 2008
Thursday, August 28, 2008
恍惚十年
我的伯伯是村里的马华公会领袖,因此我家天生是马华公会的选举行动室。每到大选、补选时,我家就贴满国阵的标志和国阵候选人的脸孔。
我跟同伴们总是跟着大人们忙贴海报、夹海报,到村头村尾挂海报。选举期间,平日冷清清的家总是变得很热闹,也总是有吃的喝的。
 我跟同伴们偶尔找来废弃的木条,在那上面画称头、画火箭、画月亮、或是跟着海报写“请投国阵神圣一票”。那时候,就像看武侠片忠奸分明,我们只知道国阵是忠的,反对党是奸的,奸人是要来破坏这个国家的。那时候,我没有听说过聂阿兹、哈迪阿旺,林吉祥听说是个只懂骂人的家伙,马哈迪和安华则是我的偶像。(有的人要笑了,可是,这毕竟是个在政治氛围中长大的孩子。况且,这孩子恋父。)
我跟同伴们偶尔找来废弃的木条,在那上面画称头、画火箭、画月亮、或是跟着海报写“请投国阵神圣一票”。那时候,就像看武侠片忠奸分明,我们只知道国阵是忠的,反对党是奸的,奸人是要来破坏这个国家的。那时候,我没有听说过聂阿兹、哈迪阿旺,林吉祥听说是个只懂骂人的家伙,马哈迪和安华则是我的偶像。(有的人要笑了,可是,这毕竟是个在政治氛围中长大的孩子。况且,这孩子恋父。)
活在忠奸分明的世界是非常美好的。那年头,整个村子充斥同仇敌忾的气氛,哪家人有亲反对党的倾向,总要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活在“忠人”中间的我,感觉就像活在安全的保护网中。
在十年前那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变局中,我第一次怀疑自己画下的忠奸界线。一直以来,我相信领袖、相信自己生存的世界、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那一天,从电视上知道自己一向敬爱的领袖被另一位自己敬爱的领袖革职,我混沌、模糊,复杂的情绪中还参杂着受骗、愤怒的感觉。
瓦解了,我铁石一般的信心。那一刻起,我不知道我该相信什么、我该相信谁。
现在回想起,我必须感激马哈迪,给了我重要的政治启蒙教育。在信心的断桓破瓦中,我一点一点地重建自己的信念。终于,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告诉自己,这个世界没有忠奸之分,只有胜负之分。
没有忠奸之分的世界是险恶的。它自然没有以前正邪分明的世界那么美好,可是,除非我愿意一生活在幻梦中,我就必须清醒地接受,没有正邪之分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
站在峇东埔补选计票中心的草场上,目睹无数张脸孔为安华的胜利疯狂欢呼,我想,十年前的那一个变局,非但启蒙了在马华公会的政治气氛中长大的我,也启蒙了无数个像我一样愚昧的马来西亚人。我必须向过去一直启迪我的评论人、新闻工作者、公民组织工作者致敬,你们辛勤的浇水施肥,终于让民主意识在这片贫瘠的土地开花。
峇东埔补选日的早晨,我在投票中心见到的选民,无论是马来人、华人还是印度人皆是一幅老板样,就跟我在3月8日的大选的早晨见到的一样。
选民终于意识到了,他们手中的一票可以教训嚣张妄为的政治人物、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以左右国家的前途。像进发一直强调的,民主是个empowering the people的过程,当人民感觉自己充满力量,这个国家的民主就开始抬头了。
在投票中心奔走的时候,我还在感觉到,以前人们投反对票还需闪闪缩缩,可是,现在的情况是,表态支持在野党、投选在野党可以光明正大,倒是投选腐朽已极的执政党才是需要缩头缩尾的。原因可能是,3月8日过后,大家都发现到,原来大家心里想的都是一样的,既然如此就没什么好怕了。
民主之花终于开了,这是个赏花的季节。花开了之后,就是等待收成时。
我必须以十年前的启蒙教育警惕自己,这个世界没有忠奸、正邪之分,安华只是人民委托以改变国运的领袖,而非永远只有光明面的Superman或Batman。安华和民联各号打着正义的旗帜称雄的人,皆有显露黑暗面的可能性,因此,制度的确立才是最重要的。惟有领袖们争相谈论如何改革体制,让司法、媒体、反贪局独立,民意才算结出甜蜜的果实。
人民用十年时间,让民主开出花来,下一个十年,一定也能让民主开出甜蜜的果实来。我们的世界没有dark knight,我们相信自己。
我跟同伴们总是跟着大人们忙贴海报、夹海报,到村头村尾挂海报。选举期间,平日冷清清的家总是变得很热闹,也总是有吃的喝的。
 我跟同伴们偶尔找来废弃的木条,在那上面画称头、画火箭、画月亮、或是跟着海报写“请投国阵神圣一票”。那时候,就像看武侠片忠奸分明,我们只知道国阵是忠的,反对党是奸的,奸人是要来破坏这个国家的。那时候,我没有听说过聂阿兹、哈迪阿旺,林吉祥听说是个只懂骂人的家伙,马哈迪和安华则是我的偶像。(有的人要笑了,可是,这毕竟是个在政治氛围中长大的孩子。况且,这孩子恋父。)
我跟同伴们偶尔找来废弃的木条,在那上面画称头、画火箭、画月亮、或是跟着海报写“请投国阵神圣一票”。那时候,就像看武侠片忠奸分明,我们只知道国阵是忠的,反对党是奸的,奸人是要来破坏这个国家的。那时候,我没有听说过聂阿兹、哈迪阿旺,林吉祥听说是个只懂骂人的家伙,马哈迪和安华则是我的偶像。(有的人要笑了,可是,这毕竟是个在政治氛围中长大的孩子。况且,这孩子恋父。)活在忠奸分明的世界是非常美好的。那年头,整个村子充斥同仇敌忾的气氛,哪家人有亲反对党的倾向,总要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活在“忠人”中间的我,感觉就像活在安全的保护网中。
在十年前那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变局中,我第一次怀疑自己画下的忠奸界线。一直以来,我相信领袖、相信自己生存的世界、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那一天,从电视上知道自己一向敬爱的领袖被另一位自己敬爱的领袖革职,我混沌、模糊,复杂的情绪中还参杂着受骗、愤怒的感觉。
瓦解了,我铁石一般的信心。那一刻起,我不知道我该相信什么、我该相信谁。
现在回想起,我必须感激马哈迪,给了我重要的政治启蒙教育。在信心的断桓破瓦中,我一点一点地重建自己的信念。终于,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告诉自己,这个世界没有忠奸之分,只有胜负之分。
没有忠奸之分的世界是险恶的。它自然没有以前正邪分明的世界那么美好,可是,除非我愿意一生活在幻梦中,我就必须清醒地接受,没有正邪之分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
站在峇东埔补选计票中心的草场上,目睹无数张脸孔为安华的胜利疯狂欢呼,我想,十年前的那一个变局,非但启蒙了在马华公会的政治气氛中长大的我,也启蒙了无数个像我一样愚昧的马来西亚人。我必须向过去一直启迪我的评论人、新闻工作者、公民组织工作者致敬,你们辛勤的浇水施肥,终于让民主意识在这片贫瘠的土地开花。
峇东埔补选日的早晨,我在投票中心见到的选民,无论是马来人、华人还是印度人皆是一幅老板样,就跟我在3月8日的大选的早晨见到的一样。
选民终于意识到了,他们手中的一票可以教训嚣张妄为的政治人物、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以左右国家的前途。像进发一直强调的,民主是个empowering the people的过程,当人民感觉自己充满力量,这个国家的民主就开始抬头了。
在投票中心奔走的时候,我还在感觉到,以前人们投反对票还需闪闪缩缩,可是,现在的情况是,表态支持在野党、投选在野党可以光明正大,倒是投选腐朽已极的执政党才是需要缩头缩尾的。原因可能是,3月8日过后,大家都发现到,原来大家心里想的都是一样的,既然如此就没什么好怕了。
民主之花终于开了,这是个赏花的季节。花开了之后,就是等待收成时。
我必须以十年前的启蒙教育警惕自己,这个世界没有忠奸、正邪之分,安华只是人民委托以改变国运的领袖,而非永远只有光明面的Superman或Batman。安华和民联各号打着正义的旗帜称雄的人,皆有显露黑暗面的可能性,因此,制度的确立才是最重要的。惟有领袖们争相谈论如何改革体制,让司法、媒体、反贪局独立,民意才算结出甜蜜的果实。
人民用十年时间,让民主开出花来,下一个十年,一定也能让民主开出甜蜜的果实来。我们的世界没有dark knight,我们相信自己。
Saturday, August 16, 2008
我来到这里
他们付了钱,就匆匆忙忙走出大门。“哎,这里,这里。”柜台的印尼女工把他们喊住。我正穿着t-shirt和短裤,向柜台借一个三叉插座。
他们重新走进门来,包着头巾的,那女的,偷偷瞄我一眼,像腼腆的日本娃娃一样,夹着脚低着头拖着她身上那笼传统衣裙快步上楼。
“你要的就是这个吗?”我的视线向印尼女工所在之处驶去中途,停在男人的身上两秒钟。友族。又一个友族同胞。
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尽管入门处没有很窄,可是进出时总有一种压迫感,我开始在担心,下一次碰上的,是什么人。或者说,什么男人。
我因一场造神的补选来到这里。这是一间用半独立式双层排屋改装的小旅馆,楼上楼下都是出租用的房,40元到90元一晚都有,我的是75元一晚的,还需与人共用厕所。我是个没有星级酒店,住73元的房间也可以的人,只要房间和床干净就好(其实后来我想,哪有酒店床是干净的?)。第一眼看它,床和摆设都还挺新的,比我想象中理想,我没有理由不满足。
可是,自从我知道这是别人开心的地方,我就开始不开心了。
他们重新走进门来,包着头巾的,那女的,偷偷瞄我一眼,像腼腆的日本娃娃一样,夹着脚低着头拖着她身上那笼传统衣裙快步上楼。
“你要的就是这个吗?”我的视线向印尼女工所在之处驶去中途,停在男人的身上两秒钟。友族。又一个友族同胞。
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尽管入门处没有很窄,可是进出时总有一种压迫感,我开始在担心,下一次碰上的,是什么人。或者说,什么男人。
我因一场造神的补选来到这里。这是一间用半独立式双层排屋改装的小旅馆,楼上楼下都是出租用的房,40元到90元一晚都有,我的是75元一晚的,还需与人共用厕所。我是个没有星级酒店,住73元的房间也可以的人,只要房间和床干净就好(其实后来我想,哪有酒店床是干净的?)。第一眼看它,床和摆设都还挺新的,比我想象中理想,我没有理由不满足。
可是,自从我知道这是别人开心的地方,我就开始不开心了。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