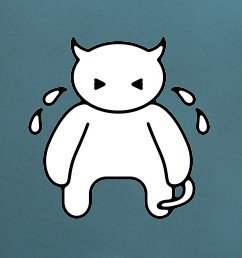在记者面前,他激动地为女儿的名声辩护。说着说着,他突然问起大头墨水笔。
在记者面前,他激动地为女儿的名声辩护。说着说着,他突然问起大头墨水笔。接过大头墨水笔后,他在白板上画上一个半圆的人头,然后又画上另一个半圆的人头,说:“这是我,这是我太太,我们从不相识到结婚……”边说,他边在两个半圆的人头中间写上女儿的名字,继说:“直到第一个女儿出世后,我们的生命才算完整。”
那一刻,白板化成了青葱的草原,我看到了一个在风中孤立饮泣的父亲。父亲脚下,是女儿遗留的200多块碎片。
她“轰”地一声消失,一夜之间成为头条新闻人物。每个人都想知道更多,关于她;每个人都想从中窥探隐匿其中的政治乱象,可是,没有人真正在乎她的价值、她存在的意义、她生命的重量。她的死,仿佛就为了乱象的显现。
父亲的表述,在一片喧哗浮夸的议论声中,显得格外真实而厚重。在父亲画出“完整的家庭”的时候,她终于摆脱了外界的诸般描绘,回复到新生婴儿的模样,重拾自己的价值。
无论女儿的死牵连多广,在父亲的心目中,没有什么比“女儿死了”这个事实更重要。
父亲节刚过。我在今年的父亲节前,看到了一个父亲,一个伤心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