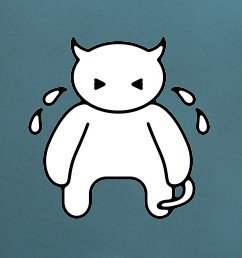那一天,我们决定到森林里的高脚棚留宿。决定了之后,我们就跟着简单的地图的指示出发,背包里只有简单的装备,瓶装水、手电筒,可能还有一本书,脚下穿的是廉价的球鞋。
走在错杂的草丛里,我的心情应该是兴奋和担忧参杂的。过程我已忘了,我想路上我们应是说话、谈笑、沉默、说话、谈笑、沉默,偶尔谁跟着谁哼起一首什么歌。我们在天黑之前抵达,赶得及在残阳下欣赏木棚旁的溪流。溪流清澈见底,充满灵气,像一只正在起舞的土色水蛇。
高脚棚里还有两个白男子和一个白女子。互相礼貌问好过后,我们坐在洞开的木墙边,看夜幕渐渐笼罩。
夜幕渐渐笼罩。我们被漆黑的树影包围。夜那么黑,我从未见过那么黑的夜。你说待会我们会见到什么动物?我问。我希望见到老虎。我中学时听隔壁叔叔说起老虎身上的骚味在数十公尺外都可嗅到的传言,对这种无从亲近的动物有莫名的好奇。
在等待虎的时间里,我可能跟你们说起了我在六岁那年从虎口里逃生的故事。
那一年陌生的父母亲把我带到吉隆坡动物园游玩,那时的虎养在深潭里,人就伏在栏杆往下望。这对奇怪的夫妇要我自个儿坐在栏杆上拍照,我想起隔壁叔叔曾跟伯伯说起有人在动物园被虎咬死的故事,说什么也不肯。
很多年后告诉伯伯这事,伯伯大呼“好险”,大赞我机灵,可是,当时的我只得到一句“没用”的指责和几个白眼。我一直相信,如果当时我没有冒着被骂“没用”的风险坚持己见,我已经掉入深潭,被虎群撕裂、分吃了。这样死了倒没什么,只是可怜伯伯疼我一场。
期待中的虎并没有出现,倒是来了一只鼠鹿。我没有真切地见到鼠鹿饮水的画面,只在白女人呼叫“rat”时,见到一只棕白色的山老鼠在木板架上快速窜逃。
等待的夜很长,自称米高的白男人邀我们一起下楼走走。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后,决定跟着他冒险下楼。我跟在米高后面,即兴奋又害怕,森林那么陌生那么黑,我们只靠小小的电筒照明。我们蹲在小径上,米高让我们把电筒关上。
“你看,那是什么?”磷光,神秘的磷光,这里,那里,草丛里的磷光像神迹一样,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的身体消失在黑幕中,神秘的光照亮潜伏在身体里的灵魂。那一刻,我想我们闯进了灵界。
没多久我们就退回到自己的世界。森林里下起了雨。雨势越来越大,我们坐在窗边,看雨从高高的大树落下。我想象老虎、鼠鹿被淋湿、躲雨的样子,想象整座森林被雨侵袭的样子,心好像被雨润湿了,盈满一种莫名的喜悦。
高脚棚里没有人说话。这座木棚仿佛是整座森林唯一的静态。就这样,我们在森林大雨中,度过一个喧闹而宁静的夜。
我一直好想用文字记下这个九年前的夜晚,可是每次提笔都只是开了个头,就写不下去。最近我越来越担心,在脑海里收藏起来的珍贵记忆会瞬间消失,终于决定用文字将那些曾经感动过我的画面保存起来。事情已经发生那么久,记忆已经不可靠了,这篇文字是记忆和想象的结合体。
Monday, November 15, 2010
Subscribe to:
Commen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