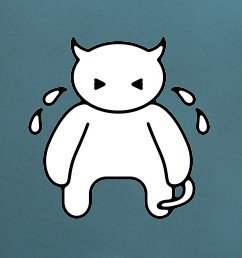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大家都叫他“黄生”。自从迎新周时在小货车上跟他聊过几句后,每回遇见他,我都会小声朝他叫声“黄生”,脚,总还是不停歇地走自己的路,好像这么叫一声,只是借意抬抬脚,跨过心里头的一条横栏。
离开数年,校园早已物非人非,可是,那天在图书馆,我竟然瞥见他--黄生。还是老样子,还是一支导路杖,仿佛时针围着他周转,时间一刻也没有从他身上移走。我想跑前去打个招呼问问近况,可是,我没有。
我不怕孤独,所以,就算他看起来很孤独,我也从未真正觉得他需要一个朋友、一些声音。直到,直到我自己盲了双眼。
托隐形眼镜的福,我盲了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这段时间,刺痛感不断在挑战我的忍耐力,眼泪川流不息,仿佛眼里有个失恋的人立意要把身上最后的盐份和水份流尽。
痛分不出去,我能依傍的,只有朋友的肩膀和医生的本事。
失明加失眠的晚上,我那双模仿咸蛋超人造型包扎的双眼,像两根毒针一样,久久地刺痛着我。我想要一把声音,可是,亲爱的朋友正沉沉睡着。手指摸上了电话的键盘,又无助地放开。盲了双眼,我就连拨电话和躲在一旁说悄悄话的能力也没有。
比刺痛感更难受的感觉,是无助。因为我盲了,朋友们不得不告假当我的导路杖。我抗拒成为麻烦制造者,可是却无法逞强说“不”,因为我真的需要。
孤傲的迷幻高台,冰消瓦解。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我看见了人的脆弱。我看见了你,黄生。
Monday, May 29, 2006
Wednesday, May 24, 2006
眼睛吃人事件
Tuesday, May 23, 2006
太阳天天新
 20060310
20060310反油起价示威。
一个油漆工人
遇见一群镇暴队员
在双峰塔下
同样的太阳天天从东方升起,可是在新闻从业员的世界,太阳是天天新的。每天从收伏倦意的床爬起来后,我们每天都要向四面八方出发,去寻找不同的太阳。
太阳是天天新的,所以我们每天的内容都和昨天不一样。昨天是沙里尔辞职事件、前天是景观大桥课题、大前天是校长贪污现象、大大前天是汽车入口准证风波、今天是涉贪国会议员自圆其说怪诞。每一天,我们都在不同的路上奔走。
太阳天天都是新的,所以任何轰动全民的大事件皆一纵即逝。去年闹开的汽车入口准证事件、裸蹲案今天都成了过眼云烟;前不久占尽报章篇幅的裸蹲案也已经烟消云散;闹得沸沸扬扬的景观大桥课题,不出两星期即风平浪静。每一个曾经让我们费尽心思追赶、牵引、指挥的太阳,都在时间的驱逐下,消失在新闻的荒野。
放牧太阳的我们,精疲力竭、笔枯舌干,为的是赶太阳上子午线大跳草裙舞,可是,时间一到太阳即不留痕迹地从子午线上消失,第二天,我们又重复昨天的作业,我们昨天所做的一切,对今天留下任何意义了吗?
昨天,头也不回地走了,少有人问起,也少有人记取,更少人去正视、去作出改变。新闻,真的改变什么了吗?到最后,我们就连跳草裙舞跳得最起劲的太阳如何停步谢幕都记不了,可不是?谁记得汽车入口准证课题最后闹出什么结果了?
记者天天为不同的太阳奔走、读者天天对着新鲜出炉的新闻长吁短叹,可是说到底,昨天的新闻和今天的新闻确实有很大落差吗?我枯竭的笔知道,它天天都在复述相同性质的故事,不同的只是故事里头的主角。
媒体人清楚不过了,媒体,除了是新闻的追随者,也是新闻的指挥者和创造者,与其跟着“太阳天天新”的幻影在新闻的荒野兜圈子,何不奋力阻挡新闻无疾而终?我们总得让跳草裙舞的太阳学会如何完满谢幕。
阴沉的星期天
哦,星期天,阴沉的星期天。阴沉的女声不断预告着一个悲情故事。装满红椅子的视听室跟着阴气沉沉。来了。镜头从海峡慢慢向大桥挪近,踏着金球的老鹰从右下角冒现。这一秒钟开始,我喜欢上了这部影片。
镜头去到一间叫Szabo的餐厅。乘坐豪华房车来到的老男人,叫了牛肉卷,点了这一首《阴沉的星期天》(Gloomy Sunday)。音乐响起时,他满意地笑了:“一切都跟以前一样。”
这一天是他的八十岁生日,侍者端来了蛋糕。一切看来是多么美好。下一秒钟,镜头指使他瞥见桌上一张女人的照片,性感、美丽、笑嫣如花。再下一秒钟,他倒地死亡。怎么一回事?每个红椅子上的人都迫切地等待着影片告知真相。可是负责讲故事的机器,偏偏选在这时候罢工。
那一天的我,怅然若失。老人的死因谜团,像一只刁蛮的蜜蜂,嗡嗡嗡,在耳边缠绕不去。负责放映的鬼佬承诺,他会努力找完好的片子回来重映一次。我等。后来鬼佬大概忘了他的承诺,竟学《阴沉的星期天》,突告罢工。
马大欧亚研究院国际电影放映会的死因之谜,嗡嗡嗡,在耳边缠绕不清。坐在研究院的木椅子上,我写了一封反馈信。投函时,我深知,我在这个校园的部分记忆,已经一去不复返。
鬼佬和他的同伴后来转在国家电影发展机构播映影片,时间仍定在每个星期三晚。我嫌太远,一直没去。不幸离得那么远,坏消息还是传了过来:鬼佬和同伴播放的国际电影被认为是黄色影片,遭指示停播。
后来,我在一家光碟店遇上了她--《阴沉的星期天》。一首真诚、赤裸裸的曲子可以杀人,你相信吗?《阴沉的星期天》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我为荒唐事笑得眼泪直流。鬼佬,你一定也一样。
镜头去到一间叫Szabo的餐厅。乘坐豪华房车来到的老男人,叫了牛肉卷,点了这一首《阴沉的星期天》(Gloomy Sunday)。音乐响起时,他满意地笑了:“一切都跟以前一样。”
这一天是他的八十岁生日,侍者端来了蛋糕。一切看来是多么美好。下一秒钟,镜头指使他瞥见桌上一张女人的照片,性感、美丽、笑嫣如花。再下一秒钟,他倒地死亡。怎么一回事?每个红椅子上的人都迫切地等待着影片告知真相。可是负责讲故事的机器,偏偏选在这时候罢工。
那一天的我,怅然若失。老人的死因谜团,像一只刁蛮的蜜蜂,嗡嗡嗡,在耳边缠绕不去。负责放映的鬼佬承诺,他会努力找完好的片子回来重映一次。我等。后来鬼佬大概忘了他的承诺,竟学《阴沉的星期天》,突告罢工。
马大欧亚研究院国际电影放映会的死因之谜,嗡嗡嗡,在耳边缠绕不清。坐在研究院的木椅子上,我写了一封反馈信。投函时,我深知,我在这个校园的部分记忆,已经一去不复返。
鬼佬和他的同伴后来转在国家电影发展机构播映影片,时间仍定在每个星期三晚。我嫌太远,一直没去。不幸离得那么远,坏消息还是传了过来:鬼佬和同伴播放的国际电影被认为是黄色影片,遭指示停播。
后来,我在一家光碟店遇上了她--《阴沉的星期天》。一首真诚、赤裸裸的曲子可以杀人,你相信吗?《阴沉的星期天》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我为荒唐事笑得眼泪直流。鬼佬,你一定也一样。
Thursday, May 11, 2006
Monday, May 08, 2006
我的自我批判
网络新闻和主流媒体最让作者开心或不开心的地方是,文章刊出后,立即就可以得到读者的反馈。读者可能批评你、责难你、鼓励你、称赞你,不管读者对你的评价如何,文章的作者既然是你,你就得硬着头皮面对,由不得你害羞躲避。
我大概是个害羞和脆弱的人,名字被读者提起时,总是紧张兮兮的。最近我因报道了一些乏人碰触的课题,被读者冠上“正义”的礼帽。飘飘然之余,不安之感油然而生。我想我是心虚了。
网络新闻是没有木棍和绳子的媒体新疆界,所以,记者可以毫无顾忌地敲打键盘,据实报道所见所闻。因此我想,我们比主流媒体更大胆、更理直气壮、更豪气干云,是理所当然的,不是什么值得吹捧传颂的事情。哪天网络媒体人无法理直气壮,那才是必须敲锣打鼓尽告知交的大事件。
网络媒体人和主流媒体人处在不同的起跑点,因此,用新闻内容来比较“正义”程度,对主流媒体人有欠公平。主流媒体人在一定的限制下作业,天天在新闻线上走钢索;比较起来,走在大桥上的网络媒体人,要博得“正义”的礼赞,实是无须耗费吹灰之力。
赞赏网络媒体人正义,分明是多此一举。我们应该把正义的礼赞,献给那些在限制中作业,而又能坚定职守、冲破局限的主流媒体人才是。
一些国家的媒体人走在悬崖中间的钢索上,踏错一步,都有可能粉身碎骨,可是尚见许多孜孜不倦的身影,默默推动着新闻自由的巨轮,比如中国《河南商报》的顾问马云龙、《中国青年报》的资深编辑李大同。我国媒体人走的钢索,下方还有高床软枕准备接护,理应学着更理直气壮一些才是。
就连身在中国的马云龙都说了,“我们永远不能声明放弃打老虎的权利”,身在民主国度的我们又怎能轻易放弃信守新闻专业的权利?
愿趁着5月3日世界新闻日,与全体马来西亚媒体人共勉之。
(原刊《东方日报》生活资讯“晒网打鱼”专栏)
我大概是个害羞和脆弱的人,名字被读者提起时,总是紧张兮兮的。最近我因报道了一些乏人碰触的课题,被读者冠上“正义”的礼帽。飘飘然之余,不安之感油然而生。我想我是心虚了。
网络新闻是没有木棍和绳子的媒体新疆界,所以,记者可以毫无顾忌地敲打键盘,据实报道所见所闻。因此我想,我们比主流媒体更大胆、更理直气壮、更豪气干云,是理所当然的,不是什么值得吹捧传颂的事情。哪天网络媒体人无法理直气壮,那才是必须敲锣打鼓尽告知交的大事件。
网络媒体人和主流媒体人处在不同的起跑点,因此,用新闻内容来比较“正义”程度,对主流媒体人有欠公平。主流媒体人在一定的限制下作业,天天在新闻线上走钢索;比较起来,走在大桥上的网络媒体人,要博得“正义”的礼赞,实是无须耗费吹灰之力。
赞赏网络媒体人正义,分明是多此一举。我们应该把正义的礼赞,献给那些在限制中作业,而又能坚定职守、冲破局限的主流媒体人才是。
一些国家的媒体人走在悬崖中间的钢索上,踏错一步,都有可能粉身碎骨,可是尚见许多孜孜不倦的身影,默默推动着新闻自由的巨轮,比如中国《河南商报》的顾问马云龙、《中国青年报》的资深编辑李大同。我国媒体人走的钢索,下方还有高床软枕准备接护,理应学着更理直气壮一些才是。
就连身在中国的马云龙都说了,“我们永远不能声明放弃打老虎的权利”,身在民主国度的我们又怎能轻易放弃信守新闻专业的权利?
愿趁着5月3日世界新闻日,与全体马来西亚媒体人共勉之。
(原刊《东方日报》生活资讯“晒网打鱼”专栏)
Wednesday, May 03, 2006
汗
城市里的小鸟永远都像是在赶街市似的,啾啾啾叫个不停。乡村的小鸟来到城市,一定惊讶得瞠目结舌。
鸟儿们躲在屋檐下、屋边的红毛丹树上、草坪上啾啾啾,从早到晚,非要把人烦死不可。乡村的小鸟遇见了城市的小鸟总要问的:“你们不会飞吗?为什么总呆在那里傻叫?”
《秘密花园》的作者见了我,也一定要赶我下楼的。“去去去,跳藤圈去、跑步去,天天坐在那里对着电脑,你不烦我都烦。”一定是这样的。
城市人最腻人的口头禅非“忙”莫属。工作累坏人、睡眠永远都嫌不足、衣服永远都买不够,一天24个小时,怎么切割都轮不到户外生活。躺在床上看《秘密花园》,书里描绘的户外生活的美感让我如躺针毯。
女佣妈妈送去的藤圈就像女巫的魔术棒,让苍白、冰冷、讨人厌、从来不知道饿是怎么一回事的小女孩玛莉变了一个人。汗水,浸湿了她的衣衫;洗涤了她的心灵;冲刷了她的冰冷,令她嗖地变身成为活泼好动、热血心肠的小女孩。
迅速变形的玛莉令我想起《老人与海》中那与大鱼搏斗的老人和《重庆森林》里失恋后不停跑步的金城武。后来我相信了,汗水,是一种魔法、一种药、一种心灵的救赎。
晚了,小鸟还在啾啾啾叫个不停,烦死。我让音乐挡住屋外的车声和鸟叫声,企图舞出一身汗。
后记:每次,访了真正的社会有功人士,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说:“你要好好照顾身体哦。”看过这篇文章后,如果你心里升出一把声音:是时候去呼吸大自然;是时候出外跑跑了,这篇文章也就达到了它的目的。
(原刊《东方日报》生活资讯“晒网打鱼”专栏)
鸟儿们躲在屋檐下、屋边的红毛丹树上、草坪上啾啾啾,从早到晚,非要把人烦死不可。乡村的小鸟遇见了城市的小鸟总要问的:“你们不会飞吗?为什么总呆在那里傻叫?”
《秘密花园》的作者见了我,也一定要赶我下楼的。“去去去,跳藤圈去、跑步去,天天坐在那里对着电脑,你不烦我都烦。”一定是这样的。
城市人最腻人的口头禅非“忙”莫属。工作累坏人、睡眠永远都嫌不足、衣服永远都买不够,一天24个小时,怎么切割都轮不到户外生活。躺在床上看《秘密花园》,书里描绘的户外生活的美感让我如躺针毯。
女佣妈妈送去的藤圈就像女巫的魔术棒,让苍白、冰冷、讨人厌、从来不知道饿是怎么一回事的小女孩玛莉变了一个人。汗水,浸湿了她的衣衫;洗涤了她的心灵;冲刷了她的冰冷,令她嗖地变身成为活泼好动、热血心肠的小女孩。
迅速变形的玛莉令我想起《老人与海》中那与大鱼搏斗的老人和《重庆森林》里失恋后不停跑步的金城武。后来我相信了,汗水,是一种魔法、一种药、一种心灵的救赎。
晚了,小鸟还在啾啾啾叫个不停,烦死。我让音乐挡住屋外的车声和鸟叫声,企图舞出一身汗。
后记:每次,访了真正的社会有功人士,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说:“你要好好照顾身体哦。”看过这篇文章后,如果你心里升出一把声音:是时候去呼吸大自然;是时候出外跑跑了,这篇文章也就达到了它的目的。
(原刊《东方日报》生活资讯“晒网打鱼”专栏)
Subscribe to:
Commen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