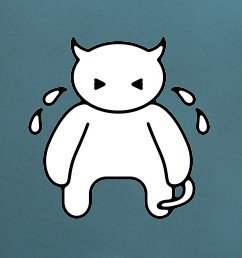他们都活在同一口钟里,没错。在框死的时间里,她只能向前,他只能倒退。在某一个时间点,他们注定擦身而过。距离消失的那一刻,天和地也跟着消失了,世界就剩那么一团交缠的影子。时间该在那一刻停顿,可是,他们毕竟是活在时钟里。她只能继续向前,他只能继续倒退,直到时钟的发条走完。
遗憾?没什么好遗憾的了,谁的人生都是一条鱼,饱满的只有中间部分,鱼头和鱼尾都乏肉可陈。能在茫茫大海中,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鱼,就已算是没有辜负大海了。时间真正作弄人的时候,是让两个前行的人各有各的起跑点和速度,永远只能互相遥望、互相追逐。
Benjamin Button跟我说,既然被编排了前行,你就继续前行吧,别指望蛋糕先生给你造个往回走的钟。往前走吧,你的遗憾可能消失在38岁,48岁,58岁,或68岁那年。
Sunday, February 22, 2009
Saturday, February 07, 2009
幻想之破灭
2月5日晚上,民联的朋友向我们传来令人沮丧的消息。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还抱有一丝希望,霹雳州务大臣尼查离开皇宫时,笑了。尽管有人说了霹雳州皇室的坏话,可我依旧对中学时代就敬重至今的苏丹阿兹兰莎存有幻想。
那年头他是我们的国家元首,温文儒雅及睿智的形象深入民心。为了在马来文作文试卷中讨考官欢心,除了背马哈迪和教育部长的语录,我们还背苏丹阿兹兰莎的讲词。
后来我上了他任名誉校长的大学,偷偷自豪。尽管那大学什么都烂,但总算还沾染了一点皇族的传统气派。毕业时我还因系院的毕业典礼没有被安排在前三天,错过从苏丹阿兹兰莎的手中接过毕业证书而怅然若失。
眼睁睁看着有幸从他手中接过毕业证书的其他系院的朋友,在我面前炫耀。他们的毕业照上,有他们和世人爱戴的苏丹的合影。
2月6日,我坐在电脑前,看着霹雳州民联政权倒下。推到霹雳州政权的,与当年颁发毕业证书给我的朋友的,是同一只手。
潘永强说,只是一场在宫廷内完成的苏丹政变,来自霹雳的黄进发自视为亡国奴,唐南发周五直驱怡保“奔丧”,霹雳州的朋友都在骂许月凤,原先敬重皇室的人,都在反省他们过去付托皇室的信任。
如果我们还能从霹雳州变天中得到什么好处,那就是它让我们认知到,透过议员跳槽换来的政府是没有民意基础的,而扩大皇权对于民主,存在的隐忧大于它可能带来的好处(便利),与其乘一事之便,给自己制造祸端,我们毋宁卧薪尝胆,待五年再战风云。争取民主,没有捷径。
霹雳州的政变,是皇权、邪恶势力与民意的交战。许多评论人已然分析出,苏丹在此具争议性局面中,该回归民意,解散州议会。收回原先的指令,解散州议会重新选举,是苏丹作为中立的统治者该做的唯一决定。道理没有太难,可曾任最高法院院长的苏丹陛下没有弄懂。
我用了五年时间,觉悟到我的大学毕业典礼,是没有遗憾的。
那年头他是我们的国家元首,温文儒雅及睿智的形象深入民心。为了在马来文作文试卷中讨考官欢心,除了背马哈迪和教育部长的语录,我们还背苏丹阿兹兰莎的讲词。
后来我上了他任名誉校长的大学,偷偷自豪。尽管那大学什么都烂,但总算还沾染了一点皇族的传统气派。毕业时我还因系院的毕业典礼没有被安排在前三天,错过从苏丹阿兹兰莎的手中接过毕业证书而怅然若失。
眼睁睁看着有幸从他手中接过毕业证书的其他系院的朋友,在我面前炫耀。他们的毕业照上,有他们和世人爱戴的苏丹的合影。
2月6日,我坐在电脑前,看着霹雳州民联政权倒下。推到霹雳州政权的,与当年颁发毕业证书给我的朋友的,是同一只手。
潘永强说,只是一场在宫廷内完成的苏丹政变,来自霹雳的黄进发自视为亡国奴,唐南发周五直驱怡保“奔丧”,霹雳州的朋友都在骂许月凤,原先敬重皇室的人,都在反省他们过去付托皇室的信任。
如果我们还能从霹雳州变天中得到什么好处,那就是它让我们认知到,透过议员跳槽换来的政府是没有民意基础的,而扩大皇权对于民主,存在的隐忧大于它可能带来的好处(便利),与其乘一事之便,给自己制造祸端,我们毋宁卧薪尝胆,待五年再战风云。争取民主,没有捷径。
霹雳州的政变,是皇权、邪恶势力与民意的交战。许多评论人已然分析出,苏丹在此具争议性局面中,该回归民意,解散州议会。收回原先的指令,解散州议会重新选举,是苏丹作为中立的统治者该做的唯一决定。道理没有太难,可曾任最高法院院长的苏丹陛下没有弄懂。
我用了五年时间,觉悟到我的大学毕业典礼,是没有遗憾的。
Subscribe to:
Commen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