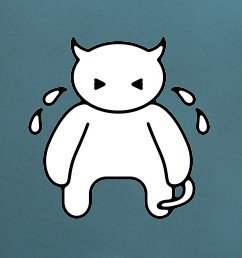Sunday, December 31, 2006
新年快乐
还有三个小时多,我们就又长大了一岁。朋友说,十多二十岁时脸上长痘痘,二十五岁过后皱纹、肚腩等老化迹象就排山倒海地来到,不曾美过,人就老了。我也有同感。想要想想什么时候的自己最美,竟有种不堪设想的感觉(期盼全盛时期会在未来)。美容师说人到25岁就会开始老化,老已经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惟有学会欣赏自己的肚腩还有二度青春期冒起的痘痘。这个圣诞,我和一群陌生人、一个陌生歌手、一场风雨还有一个塌掉的圣诞蛋糕一起度过,这个新年,我(不是刻意地)远离了喧闹的庆祝仪式,回到了无新年和旧年之分的彭亨老家静静等待它的到来。一个人或两个人守候它或任它悄然走过,人老了,节日不就是这么一回事?
Saturday, December 30, 2006
失忆城市
 拆屋子、砍树、拆古迹的哐啷哐啷声在城市的一角自顾自地响着。走过的人们,头也不抬地走过。等到哪一天他们再走过,他们总会昂一昂头,说一声:“这里什么时候多了这个建筑物?以前这里是什么?”
拆屋子、砍树、拆古迹的哐啷哐啷声在城市的一角自顾自地响着。走过的人们,头也不抬地走过。等到哪一天他们再走过,他们总会昂一昂头,说一声:“这里什么时候多了这个建筑物?以前这里是什么?” 城市像长着四只脚的动物,在时间的旷地上潜爬漫移。移动的人绕了一圈回到原地,总发现城市已经换了一个样子,想要回想城市原来的样子,记忆总像糊掉的豆腐,怎么也变不出原形。
与我们共存的物事,一点一点地消失,我们浑然不觉,直到有一天我们认真凝望城市,才发现熟悉的已成陌生、存在的已成飞絮。等到我们大梦初醒,城市往往已经失去了它独有的气质和风貌。
吉隆坡在变,在迅速地变幻。短短数周的时间,我亲眼目睹了一个村子、一片森林和蔡正木故居被毁灭的过程。它们在神手哐啷哐啷的响声中,一点一点地消失,神手撕下它们的形体,也一并撕去了吉隆坡的历史样貌。
建筑物在淌血、森林在淌血,一些人的心在淌血,可是大部分的吉隆坡人无动于衷。生活在这座已经被功利价值观催眠的城市,我费力地呼吸,培养起自己的嗅觉,准备好迎接突如其来的变故;走过时,我认真地走过,用心地看看它、记取它,在它变陌生之前,亲爱的我城吉隆坡。
Thursday, December 28, 2006
你捐钱了吗?
我们的朋友善勇和南发在这场水灾中失去了宝贵的书籍、剪报和纪录片。
无数的人失去了他们宝贵的书籍、剪报、纪录片。
杨大哥昨晚说: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卡之琳〈斷章〉”
灾难很远也很近。除了捐钱聊表心意,还有什么是更实际的行动?
隆雪华堂该是可靠的,我捐了给他们,你也可以。
他们的文告是这么说的:
捐款支票请志明收款人为: “隆雪中华大会堂” 或 “The Kuala Lumpur &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支票背面请注明“捐助水灾灾民”。捐款或物资请在2007年1月5日(星期五)之前,交到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秘书处,地址是The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No.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电话:03-22746645。
无数的人失去了他们宝贵的书籍、剪报、纪录片。
杨大哥昨晚说: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卡之琳〈斷章〉”
灾难很远也很近。除了捐钱聊表心意,还有什么是更实际的行动?
隆雪华堂该是可靠的,我捐了给他们,你也可以。
他们的文告是这么说的:
捐款支票请志明收款人为: “隆雪中华大会堂” 或 “The Kuala Lumpur &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支票背面请注明“捐助水灾灾民”。捐款或物资请在2007年1月5日(星期五)之前,交到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秘书处,地址是The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No.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电话:03-22746645。
Saturday, December 23, 2006
圣诞老人的故事
Friday, December 22, 2006
Bok House 噢 Bok House
聪明的部长说:“We feel sorry for people who are expressive... but the building had no overpowering aesthetic value.”
Thursday, December 21, 2006
大公司,在停电的夜
电视机活在我们中间,这已是无可扭转的事实。自从我爸在我四岁那年中了马票,让我们家成为村里第一家拥有电视机的住户之后,我和家人中间,便永远横着一台电视机。
在上学的那些日子,晚上短短的几个小时,是我和家人(其实也只不过是伯伯一个人)相处的时间。小学时回家会第一时间向伯伯报告一天的所见所闻,可是,上中学以后,伯伯距离我的学校生活越来越遥远,遥远得让我觉得已经没有禀报的必要。电视剧的剧情,成为我和伯伯之间仅存的话题。
电视机让我和家人有了一些共同的话题,可是却让我们越来越惰于开辟另一种沟通的方式。因此,虽然停电很可恶,但是我却喜欢夜间偶发的停电事件。
停电时,村人们失去了晚间唯一的娱乐方式---看电视,和家人谈话,成了消磨长夜的唯一方式。这时候,在黑漆漆的小客厅里,伯伯会说起遥远而勾人怀想的事情。他会说,我七个月大时突然说起了话来;四岁时他用石头子教我算术。他也会说起“大公司”,那是一种类似长屋的公共住宅,我四岁以前就住在那地方。
伯伯告诉我,大公司里头,每间屋子只有一间房,厕所是公厕,整个大公司只有两间,一在头,一在尾,所以尿桶是居家必备之物。那时候,还真的有“倒屎佬”的工作,晚上倒屎佬会出动,到公厕和每户人家的后门收溺物。还有还有,大公司附近还有个电影院,放映中港的黑白电影,观众去看电影还得自备椅子。
没有电流、电视机,大公司的人们生活一定很枯燥了。但是入夜之后,家家户户守着一盏煤油灯,说说村子的旧事、说说一天发生的事、说说刚刚上画的电影,中间没有电视机的声音,只有天上不会说话的星星,那样的生活不是很恬静美好吗?
在上学的那些日子,晚上短短的几个小时,是我和家人(其实也只不过是伯伯一个人)相处的时间。小学时回家会第一时间向伯伯报告一天的所见所闻,可是,上中学以后,伯伯距离我的学校生活越来越遥远,遥远得让我觉得已经没有禀报的必要。电视剧的剧情,成为我和伯伯之间仅存的话题。
电视机让我和家人有了一些共同的话题,可是却让我们越来越惰于开辟另一种沟通的方式。因此,虽然停电很可恶,但是我却喜欢夜间偶发的停电事件。
停电时,村人们失去了晚间唯一的娱乐方式---看电视,和家人谈话,成了消磨长夜的唯一方式。这时候,在黑漆漆的小客厅里,伯伯会说起遥远而勾人怀想的事情。他会说,我七个月大时突然说起了话来;四岁时他用石头子教我算术。他也会说起“大公司”,那是一种类似长屋的公共住宅,我四岁以前就住在那地方。
伯伯告诉我,大公司里头,每间屋子只有一间房,厕所是公厕,整个大公司只有两间,一在头,一在尾,所以尿桶是居家必备之物。那时候,还真的有“倒屎佬”的工作,晚上倒屎佬会出动,到公厕和每户人家的后门收溺物。还有还有,大公司附近还有个电影院,放映中港的黑白电影,观众去看电影还得自备椅子。
没有电流、电视机,大公司的人们生活一定很枯燥了。但是入夜之后,家家户户守着一盏煤油灯,说说村子的旧事、说说一天发生的事、说说刚刚上画的电影,中间没有电视机的声音,只有天上不会说话的星星,那样的生活不是很恬静美好吗?
Monday, December 18, 2006
来自南非的礼物
Saturday, December 16, 2006
马大boleh!
我在家中。刚刚一个在马大念经济系硕士班的家乡朋友来找我聊聊。她告诉我一个耸人听闻的事情。她说,她的系里有不少外籍人士,大部分是中东人和中国人,她在简单的接触中发现,大部分的他们不谙英语,只懂一些简单的词句,其中一名索马里亚人,自己正念着硕士课程,竟以为自己在念博士。中国朋友们做统计学的功课,可以把方的东西变成圆的,简直就像月球人降陆地球。朋友说,经济课程难得要命,还有许多算术难题要解,她很怀疑他们怎么完成课程。你说你说,马大是不是为了拉高自己在全球大学排行榜的排名,胡乱录取外籍学生?认真想想,这也不算什么耸人听闻的事,在万能的Bolehland。
Monday, December 11, 2006
一夜之间消失的村落(3)

进攻。
挣扎。
 哭泣。
哭泣。呆望。
 毁灭
毁灭.
.
.
.
冷寂。
我以为我去到了荒地,可是文字告诉我,一周前,那里原是一个住有81户人家的村落。这个村落数十年来以自己的速度和方式,附身闹市的一角,自顾自成长、呼吸,若不是突然冒出头来的什么“零木屋区计划”,也许它就可以一直以井水的姿态,在河水的世界继续生存下去。
村落与鹰阁医院相距不远。它们,一个是穷人为填饱肚子日夜挣扎的边缘地带,一个是不愁吃喝的富人送钱延续生命的地方。这一边的人们从来不奢望生病时入住鹰阁,获得上宾式的看护,他们踩着钢索却又浑不以为然,天天束衣节食却又怡然自得地在贫穷线上劳作觅活,仿佛病痛从来就是天方夜谭。
也许,朴实的生命从来就“刚刚好”,没有太多也没有太少,从天而降的幸与不幸,不在他们所能设想的范围。因此,当幸福或不幸事件降临,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没有抗拒、犹豫、推托的余地。
市议会开动的神手开动前的一秒钟,也许他们还天真地以为,灾难不会真的降临。他们耗尽最后一分力气,呼喊、哀号、抵抗,企盼行刑者的怜悯和同情,可是在狰狞的神手面前,他们的泪水和手臂,显得那么那么地渺小脆弱,仿佛只须神手轻轻的一爪,就可化为乌有。
当同情心和诸如此类的人性特点已经消亡,再没有什么是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了。神手几番转动,他们居住了数十年的村子即消失无踪,祖先的足迹、梁木的刻痕、孩童的笑声,皆和村子一并消失。一番兵荒马乱之后,一切迅速回归平静,仿佛这片土地过去五十年的历史,就此一笔勾销。
我在残桓断瓦中记录空气中的泪水、哭声、怒斥声、抵抗的力道,以为可以就此留住一点有关村落的记忆。可是比较起五十年岁月遗留下的墙和瓦、失家婴孩未来五十年的成长岁月,我那一丁点的笔墨显得那么那么地微不足道。
挥笔记录中途,墨水突告枯竭,似乎在预告着,这失落的一群,终究会被人们淡忘,他们将散失在人群中,怀抱着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与人无尤地继续讨生活。平静之后,记忆,是他们的;痛,也是他们的。
Saturday, December 09, 2006
圣诞老人骗人
我以为圣诞老人会来,在2007年凶神恶煞地走来以前。圣诞大餐的烛光点亮前,铃当声招摇着领着笑声远去。圣诞老人喜欢人多的地方。我失去了12月,失去了12月唯一的期盼。28岁是个可怕的年龄,我的已经提早到来。
Friday, December 08, 2006
你突如其来的热情
这个地方,我叫它作家。我的床去到哪里,哪里便是我的家。我是个孤僻的人,觉得生活圈子小小的就好。虽然家里住着其他一些女人,四年半来我还是只跟室友一个人好。自从室友搬离以后,我渐渐习惯独居寡言的生活。家变成没有笑声的游乐场,我变成没有玩伴的游乐场顾客。我游戏的方式拍成电影一定沉闷至极,周末的玩法是睡到隔壁的厨房挥动锅铲煮午餐,然后半梦半醒地躺在床上看书,看书,看书,最后爬起来洗刷吃早餐,再躺在床上网游,写稿,写部落格。
每天工作完毕后,我都立刻溜进房里锁上自己,把外面的世界挡在门外。偶尔走进屋里看见屋友,也只是勉强地疲累地笑笑。双方大概都觉得,这样的碰面是劳神费时的。她们在于我,我在与她们,真的没有比陌路人好很多。
可是这一阵她们突然对我亲切善良起来。见了面她们都问我要搬去哪里,那边地方好吗。这一天她们敲起了我的门。曾经跟我有过小过节的乐碧克捧着一个没用过的电饭锅站在门外,说这个电饭锅得留给你,因为我12月要到澳洲去了。她身边的希拉帮她说:“乐碧克快要嫁到澳洲去了。”我在慌忙中说恭喜。希拉又在慌忙中递过一张青色封套的贺卡,妩媚地笑说:“这是我跟乐碧克送给你的,你真是一个友善的女孩,我们都会很想念你。”乐碧克陪着说:“你答应我们,走后一定要回来看我们,好吗?”接着希拉又启动她妩媚的红唇说:“你一定要答应,让我请你吃一顿披萨,哪天我们叫Domino's Pizza回来吃好吗?”
站在突如其来的热情面前,我有点尴尬有点不知所措。她们口中的我明明不是现实中的我。在这屋里的我,从来就是一个冷漠沉静的女孩,谈不上友善,更够不上让她们想念。当乐碧克说起“一定要回来看我们哦”,我茫然无措、呆若木鸡,不知如何作答。
她们弹奏的这一首最后的插曲,我以为我永远也不会听得明白。后来我终于想起,我也总是离别前,突如其来地亲切起来。在别人转身离去前,为他在身后擦亮一盏照明的柴火,许是人之常情。别以为留柴火的人是真善美的化身,他们不过是自私地想要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而已。愿意在末时擦亮一点柴火已经算是相当周到了,去的人,你又何必去计较虚实真假?
每天工作完毕后,我都立刻溜进房里锁上自己,把外面的世界挡在门外。偶尔走进屋里看见屋友,也只是勉强地疲累地笑笑。双方大概都觉得,这样的碰面是劳神费时的。她们在于我,我在与她们,真的没有比陌路人好很多。
可是这一阵她们突然对我亲切善良起来。见了面她们都问我要搬去哪里,那边地方好吗。这一天她们敲起了我的门。曾经跟我有过小过节的乐碧克捧着一个没用过的电饭锅站在门外,说这个电饭锅得留给你,因为我12月要到澳洲去了。她身边的希拉帮她说:“乐碧克快要嫁到澳洲去了。”我在慌忙中说恭喜。希拉又在慌忙中递过一张青色封套的贺卡,妩媚地笑说:“这是我跟乐碧克送给你的,你真是一个友善的女孩,我们都会很想念你。”乐碧克陪着说:“你答应我们,走后一定要回来看我们,好吗?”接着希拉又启动她妩媚的红唇说:“你一定要答应,让我请你吃一顿披萨,哪天我们叫Domino's Pizza回来吃好吗?”
站在突如其来的热情面前,我有点尴尬有点不知所措。她们口中的我明明不是现实中的我。在这屋里的我,从来就是一个冷漠沉静的女孩,谈不上友善,更够不上让她们想念。当乐碧克说起“一定要回来看我们哦”,我茫然无措、呆若木鸡,不知如何作答。
她们弹奏的这一首最后的插曲,我以为我永远也不会听得明白。后来我终于想起,我也总是离别前,突如其来地亲切起来。在别人转身离去前,为他在身后擦亮一盏照明的柴火,许是人之常情。别以为留柴火的人是真善美的化身,他们不过是自私地想要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而已。愿意在末时擦亮一点柴火已经算是相当周到了,去的人,你又何必去计较虚实真假?
Tuesday, December 05, 2006
一夜消失的村落(2)
Friday, December 01, 2006
一夜消失的村落
喝茶啰
Mksow打电话来说,茶水以外主人还会炒面宴客。为免造成食物浪费,大家一起去吃饱饱啦。世上出其不意的事多着呢,也许吃喝一顿媒体就有救了呢。去啦去啦。
“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
活动日期:12月1日-星期五
时间:傍晚七时正
地点:吉隆坡安邦路马华公会总部
“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
活动日期:12月1日-星期五
时间:傍晚七时正
地点:吉隆坡安邦路马华公会总部
Subscribe to:
Comments (Atom)


 “非洲妈妈”辣椒酱,很Nando's的感觉。瓶子说尝它可以尝到非洲的温暖。
“非洲妈妈”辣椒酱,很Nando's的感觉。瓶子说尝它可以尝到非洲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