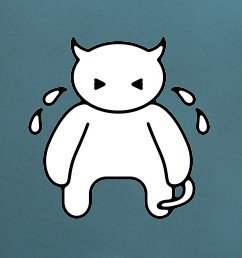在电影院中被Glen的爆发力震撼的时候,我重新发现了自己在忧伤的时候喜欢被摇滚乐包围的原因。
我知道你,我心中黑色的灵魂。当一切意义的爱背离你,你慌乱迷茫地在世界流窜,没有光线的幽谷,是你唯一的出口。
乐手的嘶喊释放你内心最后一点深藏的忧伤。鼓声狠狠地敲击它们,吉他声热烈地诅咒它们。“谎言,谎言,谎言……”你嗅着自己身上尸体的味道,跟着音乐一同旋转,下沉,旋转。
下沉,旋转,下沉,旋转。
下沉,旋转。
直到耗尽力气为止。
Friday, May 30, 2008
Sunday, May 18, 2008
终于感动了(?)
我的同情心已经被可怕的情兽吃掉了,我以为。
三年前,我在烟霾笼罩入侵的办公室书写烟霾,猛然在办公室决堤。一次又一次,我到木屋区采访时跟着嘶喊的居民落泪。可是,缅甸风灾、四川地震发生,我没有真正动容过。距离是原因,我以为。
可是,早前我国出现了一个摄录了军人被虐的短片,同事说可怕,我说,“没什么”。于是我知道,同情心的神秘失踪,无关灾难的国籍。
可是今天,四川救灾工作超过100个小时,我第一次被报纸的画面和描述感动。婴儿奇迹生还、军人奋勇救人、母亲死前哺乳救孩子,人类求生和救生的意志力,令远在马来西亚的我热泪泛滥。我以为人性的光辉会照耀我的下半天,可是一名中国记者朋友的一封电邮——“终于只剩下感动了”,终究换来我阴沉的下半天。
灾区有它光辉的一面,也有它黑暗的一面。你以为灾区光辉弥漫,只因为报纸和电视没有告知你另一幅景象。这篇朋友转发的文章再度坚定了我的信念:在最无助的时候,也别“全力以赴”信任政府,尤其是纪录败坏的政府。
中国媒体被牢牢钳制,可是中国记者还是通过了网络的力量,告知读者另一部分的真相。天灾人祸当前,我国的媒体除了突出感人的画面,是否也可以适时发挥它监督的作用?
大地震天灾变人祸 悲伤转愤怒
博讯 2008年05月16日 > > 北京XX报记者成都假日酒店报道:
送到北京的两篇稿子都被总编压了下来,那可是两位记者辛苦地在第一线奔波了近20个小时的结果,稿子上凝聚了灾民的血和泪,我能不愤怒。
我的愤怒变得微不足道,眼看这场天灾已经慢慢变成人祸,灾民们也渐渐出离悲伤,而感觉到了愤怒。政府的宣传正比救灾还要猛烈地扑向每一个中国人,就像他们在媒体上宣传的那样已经不惜一切代价和全力以赴了,只是每一天都在增加部队和扩大救援规模,让人不能不怀疑第一天就宣称“不惜一切代价”的政府既然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全力以赴和“不惜一切代价”了,为什么第二天还会再次扩大规模,增派部队。好在现在全国的媒体被封口了,要求宣传积极和正面的。所以,虽然整整一晚上,又有无数灾民在等待救援中悄悄死去,媒体的宣传依然是以“总理吃的是馒头和榨菜”为主,电视镜头依然是以一些感人的又救出了一个孩子为主轴。
如果说这次政府在救灾报道方面是有很大进步的,没有压制一切“负面”消息,那也不是他们想要的进步,而是这次灾难的规模实在惊人,他们已经无法控制“负面”消息的流传,加上互联网在传播中的作用。就在前天各大报纸报道一个武警战士跪地要求给自己机会再救一个孩子的时候,在整个灾区,最保守的估计那同一天有超过50位泪流满面的家长和亲人跪倒在救援人员面前,求他们救出亲人。那些凄厉的样子,让记者的眼泪没有干过,当然这些不会上到中国官方的媒体上。
糟糕的不是规模,而是这些被紧急调来的解放军战士介乎是赤手空拳来救灾的,他们勇敢,他们年轻,可是,相比较救火队员,他们不但没有必要的工具,也缺乏相应的训练。这些战士由于也缺乏救灾的心理辅导,几乎都是在边干活变流泪。记者在看到救> 灾之余集中在一起唱歌的战士们,他们没有几个脸上不是带着泪痕的。
按说,这个时候老百姓也没有话好说了,可是,灾民怎么想?救人最好的黄金三天已经过去,现在每消失一分钟,可能就有一个或者两个压在下面在灾民的生命跟着时间一起消失。记者看到,部队和救援人员虽然已经赶到了大部分现场,可是,从记者实际看到的情况,救援工作只是缓慢地进行。很多战士和救援人员面对从未见过的倒塌现场,很多时候甚至不知道如何下手。这使得站> 在一旁守候那些不知亲人生死的灾民痛苦不堪。他们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跪在救灾人员面前,苦苦哀求。
灾民的情绪开始波动,很多人已经从悲哀转向愤怒,媒体也接到通知,不要突出报道灾民激动的场面。可以想见,由于全国人民好像被媒体调动起来了,连本来应该监督政府救灾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们也宣称要放下一切“成见”,停止“反思”和“质疑”,并认为这种最可笑和愚蠢的方式就是支持政府救灾。这些使得那些根本没有看到灾区真实情况的民众一厢情愿地认为政府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天灾已经因为政府的救灾能力不济而变成人祸。看到和感觉到这些的,自然只有身处灾区的灾民。
对于为什么拖了两三天才同意日本救援队进入救灾,至今只答应了韩国和俄国,而拒绝了美国等西方多国拥有先进技术国家救灾要求,记者了解到,是因为中央高层内部有一派持“阴谋论”的以极左人士为主的高官认为,这个时候请求外援特别是美国和西方国家,虽然会救几个孩子和老百姓,但国家安全有可能受到威胁。同时也在世界人面前展示中国示弱,无法独立救灾。
记者竟然还听到一个可笑的理由,就是如果允许美国和西方的救援人员进入灾区,在救灾后他们很有可能会把灾区的详细情况捅出去,如果他们离开后在海外攻击中国的救援如何落后,如何缺乏有效的指挥,那将会在世界民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如果消息传到国内,会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对于这些把自己的脸面和手中的权力看的比灾民的命要大得多的人,灾区死多少人,都不会引起不安。当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说得不无道理,只要媒体不失去控制,他们身后始终有“放下一切反思,全力支持”政府救灾的13亿人民。至于灾民,哪怕死亡超过5万人,在他们的惯用的处理下,自然会被看成是已经把死亡减少到最低限度。接下来,可以约见,他们会动用比救灾规模还要庞大的宣传部队,弄一场给自己涂脂抹粉的文艺晚会和表彰大会,继续把那些对他们心存感激的中国人感激涕零。
然而,据记者得到的消息,要想继续愚弄灾民,掩盖自己救灾的不力和无能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记者发现一些灾民家属从网络上得知政府拖延批准外援进入的消>息后,非常气愤。以目前中国面临的地震规模来看,世界上没有国家可以独自承担,那些在这个时候要独自救灾的权贵,无异于谋杀灾民。
中央高层以温家宝为首的温和派,强烈要求请求外援。此决议两次在高层被否决和拖延。到后来温家宝和胡锦涛都作了让步,先同意日本进入。他们向政治局的解释竟然是,因为胡锦涛刚刚访日归来,两国的友好氛围还存在,日本人也更有纪律,便于控制。
实在是可悲,灾民在死亡边缘挣扎,全国人民都在情绪激昂地支持政府救灾,而政府在请求外援的时候犹豫不决,错过了最好的机会不说,还在规模上限制人家的进入,并且至今不让救灾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美国救援队进入。这些消息被目前那些守望在压在废墟前的亲人们知道后,会有什么结果,可想而知。当然现在允许日本救援队进入,中央也有担心,如果装备精良的日本队出现在中国救援队旁边,无论从效率和速度上都远远超过中国救援队的话,灾民们很可能会质疑政府为什么不让他们早点来,以及为什么不让更多外国那些拥有先进设备的救援队进入。据记者了解,这才是当局担心的,所以,日前下达指令,要慎重报道外国救援队的活动,特别是他们的成绩。
当然,可以想象,中央政府由于成功地发动了全国人民和他们一切抛弃反思和质疑,“全力以赴”信任政府,灾区就算死亡超过5万和10万,亲属们的哭声和质疑也会被全国那些再一次陷入“爱国”狂欢的“暴民”们淹没。
正如记者这两天在仍然压着无数幼小生命的学校废墟前思考的那样:如果你不幸生为中国人的孩子,那也千万不要成为灾区的孩子。
三年前,我在烟霾笼罩入侵的办公室书写烟霾,猛然在办公室决堤。一次又一次,我到木屋区采访时跟着嘶喊的居民落泪。可是,缅甸风灾、四川地震发生,我没有真正动容过。距离是原因,我以为。
可是,早前我国出现了一个摄录了军人被虐的短片,同事说可怕,我说,“没什么”。于是我知道,同情心的神秘失踪,无关灾难的国籍。
可是今天,四川救灾工作超过100个小时,我第一次被报纸的画面和描述感动。婴儿奇迹生还、军人奋勇救人、母亲死前哺乳救孩子,人类求生和救生的意志力,令远在马来西亚的我热泪泛滥。我以为人性的光辉会照耀我的下半天,可是一名中国记者朋友的一封电邮——“终于只剩下感动了”,终究换来我阴沉的下半天。
灾区有它光辉的一面,也有它黑暗的一面。你以为灾区光辉弥漫,只因为报纸和电视没有告知你另一幅景象。这篇朋友转发的文章再度坚定了我的信念:在最无助的时候,也别“全力以赴”信任政府,尤其是纪录败坏的政府。
中国媒体被牢牢钳制,可是中国记者还是通过了网络的力量,告知读者另一部分的真相。天灾人祸当前,我国的媒体除了突出感人的画面,是否也可以适时发挥它监督的作用?
大地震天灾变人祸 悲伤转愤怒
博讯 2008年05月16日 > > 北京XX报记者成都假日酒店报道:
送到北京的两篇稿子都被总编压了下来,那可是两位记者辛苦地在第一线奔波了近20个小时的结果,稿子上凝聚了灾民的血和泪,我能不愤怒。
我的愤怒变得微不足道,眼看这场天灾已经慢慢变成人祸,灾民们也渐渐出离悲伤,而感觉到了愤怒。政府的宣传正比救灾还要猛烈地扑向每一个中国人,就像他们在媒体上宣传的那样已经不惜一切代价和全力以赴了,只是每一天都在增加部队和扩大救援规模,让人不能不怀疑第一天就宣称“不惜一切代价”的政府既然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全力以赴和“不惜一切代价”了,为什么第二天还会再次扩大规模,增派部队。好在现在全国的媒体被封口了,要求宣传积极和正面的。所以,虽然整整一晚上,又有无数灾民在等待救援中悄悄死去,媒体的宣传依然是以“总理吃的是馒头和榨菜”为主,电视镜头依然是以一些感人的又救出了一个孩子为主轴。
如果说这次政府在救灾报道方面是有很大进步的,没有压制一切“负面”消息,那也不是他们想要的进步,而是这次灾难的规模实在惊人,他们已经无法控制“负面”消息的流传,加上互联网在传播中的作用。就在前天各大报纸报道一个武警战士跪地要求给自己机会再救一个孩子的时候,在整个灾区,最保守的估计那同一天有超过50位泪流满面的家长和亲人跪倒在救援人员面前,求他们救出亲人。那些凄厉的样子,让记者的眼泪没有干过,当然这些不会上到中国官方的媒体上。
糟糕的不是规模,而是这些被紧急调来的解放军战士介乎是赤手空拳来救灾的,他们勇敢,他们年轻,可是,相比较救火队员,他们不但没有必要的工具,也缺乏相应的训练。这些战士由于也缺乏救灾的心理辅导,几乎都是在边干活变流泪。记者在看到救> 灾之余集中在一起唱歌的战士们,他们没有几个脸上不是带着泪痕的。
按说,这个时候老百姓也没有话好说了,可是,灾民怎么想?救人最好的黄金三天已经过去,现在每消失一分钟,可能就有一个或者两个压在下面在灾民的生命跟着时间一起消失。记者看到,部队和救援人员虽然已经赶到了大部分现场,可是,从记者实际看到的情况,救援工作只是缓慢地进行。很多战士和救援人员面对从未见过的倒塌现场,很多时候甚至不知道如何下手。这使得站> 在一旁守候那些不知亲人生死的灾民痛苦不堪。他们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跪在救灾人员面前,苦苦哀求。
灾民的情绪开始波动,很多人已经从悲哀转向愤怒,媒体也接到通知,不要突出报道灾民激动的场面。可以想见,由于全国人民好像被媒体调动起来了,连本来应该监督政府救灾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们也宣称要放下一切“成见”,停止“反思”和“质疑”,并认为这种最可笑和愚蠢的方式就是支持政府救灾。这些使得那些根本没有看到灾区真实情况的民众一厢情愿地认为政府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天灾已经因为政府的救灾能力不济而变成人祸。看到和感觉到这些的,自然只有身处灾区的灾民。
对于为什么拖了两三天才同意日本救援队进入救灾,至今只答应了韩国和俄国,而拒绝了美国等西方多国拥有先进技术国家救灾要求,记者了解到,是因为中央高层内部有一派持“阴谋论”的以极左人士为主的高官认为,这个时候请求外援特别是美国和西方国家,虽然会救几个孩子和老百姓,但国家安全有可能受到威胁。同时也在世界人面前展示中国示弱,无法独立救灾。
记者竟然还听到一个可笑的理由,就是如果允许美国和西方的救援人员进入灾区,在救灾后他们很有可能会把灾区的详细情况捅出去,如果他们离开后在海外攻击中国的救援如何落后,如何缺乏有效的指挥,那将会在世界民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如果消息传到国内,会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对于这些把自己的脸面和手中的权力看的比灾民的命要大得多的人,灾区死多少人,都不会引起不安。当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说得不无道理,只要媒体不失去控制,他们身后始终有“放下一切反思,全力支持”政府救灾的13亿人民。至于灾民,哪怕死亡超过5万人,在他们的惯用的处理下,自然会被看成是已经把死亡减少到最低限度。接下来,可以约见,他们会动用比救灾规模还要庞大的宣传部队,弄一场给自己涂脂抹粉的文艺晚会和表彰大会,继续把那些对他们心存感激的中国人感激涕零。
然而,据记者得到的消息,要想继续愚弄灾民,掩盖自己救灾的不力和无能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记者发现一些灾民家属从网络上得知政府拖延批准外援进入的消>息后,非常气愤。以目前中国面临的地震规模来看,世界上没有国家可以独自承担,那些在这个时候要独自救灾的权贵,无异于谋杀灾民。
中央高层以温家宝为首的温和派,强烈要求请求外援。此决议两次在高层被否决和拖延。到后来温家宝和胡锦涛都作了让步,先同意日本进入。他们向政治局的解释竟然是,因为胡锦涛刚刚访日归来,两国的友好氛围还存在,日本人也更有纪律,便于控制。
实在是可悲,灾民在死亡边缘挣扎,全国人民都在情绪激昂地支持政府救灾,而政府在请求外援的时候犹豫不决,错过了最好的机会不说,还在规模上限制人家的进入,并且至今不让救灾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美国救援队进入。这些消息被目前那些守望在压在废墟前的亲人们知道后,会有什么结果,可想而知。当然现在允许日本救援队进入,中央也有担心,如果装备精良的日本队出现在中国救援队旁边,无论从效率和速度上都远远超过中国救援队的话,灾民们很可能会质疑政府为什么不让他们早点来,以及为什么不让更多外国那些拥有先进设备的救援队进入。据记者了解,这才是当局担心的,所以,日前下达指令,要慎重报道外国救援队的活动,特别是他们的成绩。
当然,可以想象,中央政府由于成功地发动了全国人民和他们一切抛弃反思和质疑,“全力以赴”信任政府,灾区就算死亡超过5万和10万,亲属们的哭声和质疑也会被全国那些再一次陷入“爱国”狂欢的“暴民”们淹没。
正如记者这两天在仍然压着无数幼小生命的学校废墟前思考的那样:如果你不幸生为中国人的孩子,那也千万不要成为灾区的孩子。
Saturday, May 10, 2008
兹证明,我快乐。
Sunday, May 04, 2008
医院的事
在卫生环境而言,新楼刚建起的马大医院自然比吉隆坡中央医院好,隔开床位的帘子是新的,床是新的,厕所是新的,护士小姐也是新的。护士小姐的制服分白、粉青、粉红和蓝色。粉青的制服配白色的头巾,粉红的制服也配白色的头巾,蓝色的制服配深蓝色的头巾(像女警),当粉青和粉红的护士走在一起,我的眼睛感觉就像是到了令人心情愉快的金马仑。爸的病房只有粉青色、白色和蓝色的护士小姐。爸喜欢蓝色的护士小姐,他说她们是一群勤快的生力军,叫一声就笑着来到你面前,老一点的粉青色护士小姐有时候还假装没听见你叫她。
无论如何,我遇见的粉青色护士都非常好,你把装粪的盆子送到冲洗的机器面前问她机器该怎么用,她还会亲切地说,“没关系,让我来”。到今天为止我只遇过一个向我飞白眼的护士小姐,我想是她的职业惯性之故,她长得特别胖。
医院的事只有几样,吃喝、小便、大便。爸还有一只左手可用,吃喝拉撒还可以自己解决,大小便的时候只需帮忙拉起帘子,再把尿壶或大便盆子递过去,站在帘子外东张西望一阵,问声“好了吗?”,好了就把尿壶拿去厕所冲洗干净,再到病床外的洗手槽用消毒肥皂洗我的手。至今我经手的便盆只接收过一些屁,有粪的便盆不巧都在我不在场的时候由护士小姐负责接送。
爸已是第四次进院,套我表姐说句,爸已是见惯(医院)场面了。他前三次入院是因为脑溢血昏迷,没节制地抽烟喝酒是导因。这一次他工作时从一楼的楼棚摔下,摔断了膝盖骨和手腕骨,现在断骨处已装了金属片、螺丝和钢线。前天坐在手术室外等爸动手术时,我就在想,手术过后爸爸的手和脚如果靠近磁铁,磁铁会不会吸住爸爸的手和脚呢?
人的身体就像一部车,坏了什么就送厂换,只是车没有痛感,人有。手术之后爸一直皱眉头说痛,那是我五天以来第一次见他皱眉头说痛。从出事到现在爸爸都没有沮丧过,也没有哭过,他说,既然如此,就只能如此而已。我是个脆弱的看护,幸好我有一个坚强的病人。
爸平日重视朋友甚于家人,几十年来除了他入院的时段,其他时间的他都属于他的朋友圈和杯中世界的。他谈起他的朋友圈总是眉飞色舞,说那是我没法明白的兄弟情。我确实没法明白,我只肯定我交的朋友远比他那些兄弟好。连续工作三十几个小时的天拖着疲累的身体到医院看望他,最近忙透的婷和富也抽空到医院陪他,阿爱载我去买粥陪我去医院、食物中毒的阿芬一病好就自己走到医院看我爸爸…他们都说,医药费的事可找他们帮忙,他们都说。爸自己的朋友,好像都有事情在忙。
除了动手术、照X-ray还需排大队、没有华人餐,马大医院的服务基本上相当好。我唯一有强烈意见的是它的停车场。每一次我在马大医院的停车场转圈时,我都在想,马大每年生产那么多优秀的工程师,为何竟设计出那么糟糕的停车场?那么糟糕的停车场是做来陷害那些心情恍惚的人的(我这么说你就知道我撞壁了)。
我爸跟几个印度人住在一块儿,因此病床周围总是热闹非凡的。爸出事之后开始看的Jetsun Pema的My Story,迄今只看了39页。只有那么一次,隔壁床的印度妻子静下来,我听见点滴“嘀嘀”的声响。
无论如何,我遇见的粉青色护士都非常好,你把装粪的盆子送到冲洗的机器面前问她机器该怎么用,她还会亲切地说,“没关系,让我来”。到今天为止我只遇过一个向我飞白眼的护士小姐,我想是她的职业惯性之故,她长得特别胖。
医院的事只有几样,吃喝、小便、大便。爸还有一只左手可用,吃喝拉撒还可以自己解决,大小便的时候只需帮忙拉起帘子,再把尿壶或大便盆子递过去,站在帘子外东张西望一阵,问声“好了吗?”,好了就把尿壶拿去厕所冲洗干净,再到病床外的洗手槽用消毒肥皂洗我的手。至今我经手的便盆只接收过一些屁,有粪的便盆不巧都在我不在场的时候由护士小姐负责接送。
爸已是第四次进院,套我表姐说句,爸已是见惯(医院)场面了。他前三次入院是因为脑溢血昏迷,没节制地抽烟喝酒是导因。这一次他工作时从一楼的楼棚摔下,摔断了膝盖骨和手腕骨,现在断骨处已装了金属片、螺丝和钢线。前天坐在手术室外等爸动手术时,我就在想,手术过后爸爸的手和脚如果靠近磁铁,磁铁会不会吸住爸爸的手和脚呢?
人的身体就像一部车,坏了什么就送厂换,只是车没有痛感,人有。手术之后爸一直皱眉头说痛,那是我五天以来第一次见他皱眉头说痛。从出事到现在爸爸都没有沮丧过,也没有哭过,他说,既然如此,就只能如此而已。我是个脆弱的看护,幸好我有一个坚强的病人。
爸平日重视朋友甚于家人,几十年来除了他入院的时段,其他时间的他都属于他的朋友圈和杯中世界的。他谈起他的朋友圈总是眉飞色舞,说那是我没法明白的兄弟情。我确实没法明白,我只肯定我交的朋友远比他那些兄弟好。连续工作三十几个小时的天拖着疲累的身体到医院看望他,最近忙透的婷和富也抽空到医院陪他,阿爱载我去买粥陪我去医院、食物中毒的阿芬一病好就自己走到医院看我爸爸…他们都说,医药费的事可找他们帮忙,他们都说。爸自己的朋友,好像都有事情在忙。
除了动手术、照X-ray还需排大队、没有华人餐,马大医院的服务基本上相当好。我唯一有强烈意见的是它的停车场。每一次我在马大医院的停车场转圈时,我都在想,马大每年生产那么多优秀的工程师,为何竟设计出那么糟糕的停车场?那么糟糕的停车场是做来陷害那些心情恍惚的人的(我这么说你就知道我撞壁了)。
我爸跟几个印度人住在一块儿,因此病床周围总是热闹非凡的。爸出事之后开始看的Jetsun Pema的My Story,迄今只看了39页。只有那么一次,隔壁床的印度妻子静下来,我听见点滴“嘀嘀”的声响。
Subscribe to:
Commen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