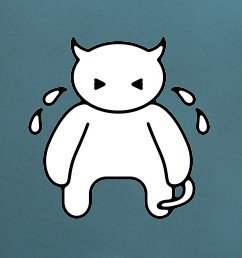我的爸爸看报纸很勤,一份报纸可以由头看到尾再由尾看到头。
可能是厚度的关系,也可能是习惯的关系,还可能是迷信第一大报的声誉,他选择看《星洲日报》。
报纸的文字是他的信仰。报纸的评论人和记者写的都是正确的,第一大报尤是。他这么相信着。“《星洲日报》说你们网络媒体都是乱来的。”“《星洲日报》分析说黄家定才适合当总会长。”“《星洲日报》说......”《星洲日报》没写的,他当然全当没发生过。
数天前翻开《星洲日报》,看见堂堂《光明日报》总编辑叶宁言之凿凿地说:“张晓卿控制的报纸会不会从此就改变中文报的角色?绝然不会!”
她还说:“不要忘记在这4家报社还有很忠於职守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有理想,有原则,多年来坚守在新闻线上鞠躬尽瘁。他们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任何人想危害华社利益,企图以私欲违反新闻操作都不容易。新闻从业员的防线,再加上广大读者的监督,不可能容许一个人或一个家族为所欲为。”我只觉得,那一天的汗,流得特别多。
堂堂一报总编辑,叶宁不去分析张晓卿和马华公会手牵手一同走之后对新闻自由的影响、张晓卿掌控马来西亚超过三分一华人的知情权之后极可能出现的“一言堂”现象,还罢了,真的,还罢了,可是亏她还说“四家报社还有很忠于职守的新闻工作者”一番令人冒汗的话,报人的堕落,该从何说起?
作为总编辑,她应该比我一个小记者更清楚,言论封锁和媒体“靠边站”(当然是靠向有权有势的这一边,不会是人民这一边)不是未来的事、不是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后会发生的事,而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事实。
看看蔡锐明去年竞选马华公会总会长时四大报的报道和评论、看看《星洲日报》报道“增建两所华小”、ASLI报告的新闻、看看“边缘论”的收场、看看“血腥星期天”的报道还有看看眼前四报处理张晓卿收购南洋的新闻,再跟《东方日报》或网络新闻作个比较,你就不难看出叶宁口中“有理想,有原则,多年来坚守在新闻线上鞠躬尽瘁的新闻工作者”如何秉持新闻从业员“崇高的原则和理想”鞠躬尽瘁地奉承掌权派。
天呀,叶宁小姐,垄断以前,报纸和报人已经靠得这么边了,垄断之后,我实在不敢想象你们会扭曲成什么样子!
今天翻开《星洲日报》,我又为爸爸担忧。有个自称从台湾嫁过来的读者,名叫“王宝珠”的,在闻名遐迩的“沟通平台”一栏写道:“看着这些人骂了五年,心中难免会想:那些一直骂张晓卿的人居心何在?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是不是恐怕中文报强大起来?当华人喉舌没有力量了,谁来传达马来西亚华人的心声?谁来延续华人生活文化?”
王宝珠呀王宝珠,政商勾结产生的畸形“团结”,岂非破坏多于建设?还有还有,你怕什么华人喉舌失去力量?你文中提及抨击张晓卿的“网络”,我奇怪你怎么没看到网络媒体写说有个叫林昌和的,还有一个叫林源德都抢着要买南洋。为什么只有张晓卿可以买,别人有钱便不能买?如果我是你,而你又跟大家一样长着一颗脑袋,我就不会这么急着上报沟通,反倒会在家里自己先用脑想一想了。
你大概跟我老爸一样,是个大报的信徒,可是我爸爸不会上网,上学也只上到小学六年级,大众传媒是他的学堂,因此我可以理解他迷信大报的心理。可是你不一样,你是个会上网、会观察各大媒体、会书写投稿的人,因此我想我必须对你有更高一点的要求(我本来还懒得理你,可是你知道吗,我那迷信报纸的爸爸可能已经拜读你的大作此刻正把你的想法和叶宁的“分析”串合起来了)。
我不是开玩笑,拜托你们,第一大报尽忠职守的高层报人和第一大报忠于君国的撰稿人,别再说些似是而非的话误导我爸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