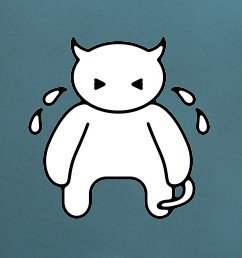想要赤脚走一圈,很想很想,小粒苹却不愿奉陪。她说,“你不要啊!你怎么知道草地里有没有害虫小蛇?”想要脱掉鞋袜的人立刻打消念头,是的,谁知道草地里没有害虫猛兽铁钉刀片玻璃?
愿望没能达成的双脚忿忿不平,已然告别发育期的脑袋爱莫能助。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小粒苹说得很清楚了:“最重要是安全。”
才不久吧,或是已经很久了,脚丫子踏上草场后,心无杂念尽情奔走。它们仅需顾虑青草、石头和泥巴,害虫猛兽铁钉刀片玻璃离它们的认知范围十万八千里。“嗯,只要不怕弄脏双脚,便可以尽情奔走”,草场和脚丫子之间的关系,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什么时候开始,事情变得不那么单纯。要考虑的项目,像叠罗汉一样越叠越高。想到害虫猛兽铁钉刀片玻璃,脱掉的欲望即刻烟消云散。“危险!危险!危险!”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警示语都贴得满满的,脚丫子准备闯入,脑袋便立即喊停。
赤脚踏青,不敢了;一个人旅行,不敢了;不顺眼便瞪人,不敢了;仗义便直言,不敢了;想走就走,不敢了;想做就做,不敢了。做什么都小心翼翼、走到哪里都眼观八方,你别扁嘴囔囔,危险啊,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对危险的认识一天一天增加,能做的事情一天一天减少。对危险的认知本身呵,就是人类最沉重的枷锁。我这么相信着,却巴巴眼束手无策,焦急得像一只坐以待毙的青蛙。
(原载今天的《东方日报》“晒网打鱼”专栏)
Monday, June 26, 2006
Monday, June 19, 2006
读者读者你在哪里?
你的读者在哪里?你无从得知,直到哪一天他们突然敲起你的门,说“嘿嘿,我在这里”。
刚入行时,我在报纸的副刊组工作,天天在吃喝玩乐的世界里打滚,一星期结束前跑一趟画展或是专访一名画家是必交的功课。由于缺乏艺术训练且感受不到读者的存在,写时不着边际心情乱乱摆,浑不知爱画的读者对画画和画家访谈这一回事有着起码的要求。
后来,评语开始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和报上的评论版,才恍然惊悟,读者呀,读者一直都在;读者无情,缺乏专业训练、经验尚浅不是交行货的藉口。为免继续难看,我找了批评我的人一起去看画、介绍画家画展,听他说画、说画坛的故事,慢慢地摸到了一点赏画、访画家的肌理(这个词也是我写画的时候学的)。
后来这名画评人成了我的好朋友,并且评我成性,看到我的文章错了一个错或一个词,就短讯相告。天天活在“惶恐”中的我,很快地丧失了涂鸦的乐趣,不过却也迅速地体悟到,读者无所不在,抱持饶幸的心理交货,或迟或早,识货的读者是找上门来的。
初来新闻线上报到,我一直没搞清楚状况,以为沿用副刊式的写法包管万无一失。第二次出征,我比较幸运,一开始就有一名闲置在家的前辈记者读者天天三五通电话来轰炸我:“你这样写不行的,得捉最新、最热暴、最关键的重点放在前头,不是由头到尾长篇叙述。”
我在挫折感和满腔不忿中继续书写,也继续忍受轰炸,最后总算成功把可爱又可气的轰炸型读者打发掉。
怎么说呢,读者是重要的,叛逆型的读者尤其重要,当他们怒气冲冲地来叩你的门,千万别把他们挡在门外,因为哄骗你进步的藤球,往往会在你打开门的那一刻,从连篇烽火的空隙处偷偷溜进你家庭院。
(原载《东方日报》生活资讯版“晒网打鱼”专栏)
后记:文章刊出后,画家朋友又来短讯了。说这次又找到一个错字。哈哈。没有错的话,我找到了那个错字。有空吗?有空一起来找找。这一次错得蛮好玩的。
刚入行时,我在报纸的副刊组工作,天天在吃喝玩乐的世界里打滚,一星期结束前跑一趟画展或是专访一名画家是必交的功课。由于缺乏艺术训练且感受不到读者的存在,写时不着边际心情乱乱摆,浑不知爱画的读者对画画和画家访谈这一回事有着起码的要求。
后来,评语开始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和报上的评论版,才恍然惊悟,读者呀,读者一直都在;读者无情,缺乏专业训练、经验尚浅不是交行货的藉口。为免继续难看,我找了批评我的人一起去看画、介绍画家画展,听他说画、说画坛的故事,慢慢地摸到了一点赏画、访画家的肌理(这个词也是我写画的时候学的)。
后来这名画评人成了我的好朋友,并且评我成性,看到我的文章错了一个错或一个词,就短讯相告。天天活在“惶恐”中的我,很快地丧失了涂鸦的乐趣,不过却也迅速地体悟到,读者无所不在,抱持饶幸的心理交货,或迟或早,识货的读者是找上门来的。
初来新闻线上报到,我一直没搞清楚状况,以为沿用副刊式的写法包管万无一失。第二次出征,我比较幸运,一开始就有一名闲置在家的前辈记者读者天天三五通电话来轰炸我:“你这样写不行的,得捉最新、最热暴、最关键的重点放在前头,不是由头到尾长篇叙述。”
我在挫折感和满腔不忿中继续书写,也继续忍受轰炸,最后总算成功把可爱又可气的轰炸型读者打发掉。
怎么说呢,读者是重要的,叛逆型的读者尤其重要,当他们怒气冲冲地来叩你的门,千万别把他们挡在门外,因为哄骗你进步的藤球,往往会在你打开门的那一刻,从连篇烽火的空隙处偷偷溜进你家庭院。
(原载《东方日报》生活资讯版“晒网打鱼”专栏)
后记:文章刊出后,画家朋友又来短讯了。说这次又找到一个错字。哈哈。没有错的话,我找到了那个错字。有空吗?有空一起来找找。这一次错得蛮好玩的。
Monday, June 12, 2006
李白上了身
八打灵再也的房子一间一间一格一格的,拘谨得像是个害羞的绅士,一到了白沙罗新村,却立刻舞步错乱,变成喝醉了酒的李白。
每一次走进白村,都像是“横闯”进去的,从来不曾感觉自己优雅地推开门礼貌地问声“有人在吗”才碎步入内。有一种人,生性敦厚老实温柔善良,但就是长成一幅对人不理不睬、对什么事都不太关心的样子,如果白村是个人,那它大概就是这一类人了。
这是什么样的一条村呢?每一次去,它都有不同的故事要说。五年前去时,遇见一群在庙里上课的学生,听了学校被深锁的故事。辗转五年,同样的故事来回复述着,期间,我又到了白村,访了一个十分静态的作家和一个喜欢和小朋友结群的画家。
访作家前,朋友说他怪,提醒我自己“拾生”,访问时,却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约访时间快到了,我在大道上跟着其它车子的尾巴如毛虫慢爬,好不容易闯向斜坡小路,像铁锤一样一路敲敲撞撞地钻进了白村。到时,约定时间已经毫不留情地把我抛在后头。可是,在地上站稳后,烦躁和惶恐即顺势开溜。五分钟前,我还在吵杂的车龙里挣扎哭嚎,这个时候,我却去到了一个就连时间也要停顿的地方。
四周那么静,由不得你烦躁和惶恐。四周那么静,静得就连传说中的怪样作家也笑脸迎人。他谈起了张爱玲、谈屋子的方位、谈女友、谈房子里一些细琐,末了,还送我出门,并且用他那一贯累累的笑容和眼神跟我道别。一切是那么恬静美好,那么出人意料。站在作家住家高墙旁的沙地上,“想要在这个地方睡一个觉”的想法油然而生。是这么一个舒服的午后噢。
后来在画家屋子的庭院,我看见了水盆里漂动的荷花、看见了画布上轻舞跳跃的精灵。走的时候,睡意突然又来袭。
于是我确认了,白沙罗新村是城里不可多得的令人舒服得想好好睡一觉的地方。李白上身的白村,每一个角落都是一个小惊喜。
我想,除了绿肥、山丘,新村也该变成保留地才对。已是满街拘谨绅士了,留我们一个李白也不算太过吧。
每一次走进白村,都像是“横闯”进去的,从来不曾感觉自己优雅地推开门礼貌地问声“有人在吗”才碎步入内。有一种人,生性敦厚老实温柔善良,但就是长成一幅对人不理不睬、对什么事都不太关心的样子,如果白村是个人,那它大概就是这一类人了。
这是什么样的一条村呢?每一次去,它都有不同的故事要说。五年前去时,遇见一群在庙里上课的学生,听了学校被深锁的故事。辗转五年,同样的故事来回复述着,期间,我又到了白村,访了一个十分静态的作家和一个喜欢和小朋友结群的画家。
访作家前,朋友说他怪,提醒我自己“拾生”,访问时,却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约访时间快到了,我在大道上跟着其它车子的尾巴如毛虫慢爬,好不容易闯向斜坡小路,像铁锤一样一路敲敲撞撞地钻进了白村。到时,约定时间已经毫不留情地把我抛在后头。可是,在地上站稳后,烦躁和惶恐即顺势开溜。五分钟前,我还在吵杂的车龙里挣扎哭嚎,这个时候,我却去到了一个就连时间也要停顿的地方。
四周那么静,由不得你烦躁和惶恐。四周那么静,静得就连传说中的怪样作家也笑脸迎人。他谈起了张爱玲、谈屋子的方位、谈女友、谈房子里一些细琐,末了,还送我出门,并且用他那一贯累累的笑容和眼神跟我道别。一切是那么恬静美好,那么出人意料。站在作家住家高墙旁的沙地上,“想要在这个地方睡一个觉”的想法油然而生。是这么一个舒服的午后噢。
后来在画家屋子的庭院,我看见了水盆里漂动的荷花、看见了画布上轻舞跳跃的精灵。走的时候,睡意突然又来袭。
于是我确认了,白沙罗新村是城里不可多得的令人舒服得想好好睡一觉的地方。李白上身的白村,每一个角落都是一个小惊喜。
我想,除了绿肥、山丘,新村也该变成保留地才对。已是满街拘谨绅士了,留我们一个李白也不算太过吧。
Friday, June 09, 2006
奇异旅程最后一天
Tuesday, June 06, 2006
5月28日这一天
我的好朋友熬过了艰辛的五年,穿上了医生袍,开始他济世救人的志业。5月28日这一天,他从砂拉越回来,我们第一时间奔椰子屋找香草皮萨。一个医生,一个摇笔的,一个“众香园”,灯光那么温暖,椰子奶昔那么冰凉,我们的话题竟从刚刚落幕的血腥场面开始。
五年前的这一天,我在校园里惊闻政党正式收购南洋报业;五年后的这一天,我亲见镇暴队武力镇压集会群众的血腥场面,528这一串平凡的号码,承载了太沉痛的悲情纪实。我们摇动的笔杆,在纸页上洒泪哀号,可是,声息却传不出电脑屏幕那一方寸格子。
静默的气氛,深罩媒体业。528报变过后,中文报业没入垄断、政党控制的漩涡之中,无从跳脱。丧失了竞争环境的中文报,陷入重大新闻不见天日的危机当中。别的新闻不说,中文报业史上最黑暗的一页--“528报殇事件”,竟然只此《东方日报》一家中文报社为文重温,其它主要报社皆静默以对,仿佛五年前的这一天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五年前的这一天,我从“报纸是文化事业”、“新闻是良心工作”的美梦中惊醒,体认到我一直崇尚的媒体事业,不过是套上了文化大衣的服务业;号称“正义至上”的报社,实乃不过逃不脱商业利益考量的商业机构。可是,五年后的今天,我发现还有不少读者迷信报社“以良心办报”,叫人不得不臣服于文字的影响力。
资讯垄断和资讯封闭之所以可怕:惰于思考之外,我们还面对独立思考能力不足的局限,因此,当重复的论调不断复述,而异议长期缺席,久而久之我们便会信以为真。柏拉图说过一个“山洞人”的故事,说几个被捆绑在山洞里的人,长年背对着一团火坐在山壁前,从未看过外面的世界,因此,他们把火光映照在山壁上的影子都错认为实体。在资讯的荒漠中过日子,莫若山洞人坐看火影子。
文学大家鲁迅认为文章可以救国,所以干脆不做医生,跑去做文章。我的医生朋友为摇动笔杆的我感到骄傲。期待哪一天我们摇动的笔杆,可以让我的朋友专心致志地救人;让我们在主流媒体奋斗的朋友们,可以快乐地摇动他们的笔杆、转动他们的长镜头。祈祷528。
(原载《东方日报》生活资讯“晒网打鱼”专栏)
P/S:重点是,《东方日报》一字不漏地刊登全文,没有删去“镇暴队武力镇压集会群众的血腥场面”这一段,很了不起了。你们知道吗,小气鬼《新海峡时报》就删走了Brian Yap专栏文章的这么一段:
"But progress is often faced with resistance from those threatened by change. Increasingly defiant voices against the IPCMC have emerged, even though the violence that broke out at KLCC last Sunday is another drop in the bucket of proof that the commission is more urgent than ever, for both the credibility of the force, as well as the safety of citizens. Its necessity cannot be overemphasised, especially in the face of hostile resistance from some quarters."
详情请参阅Amir Mohammad的blog: http://lastcommunist.blogspot.com/
五年前的这一天,我在校园里惊闻政党正式收购南洋报业;五年后的这一天,我亲见镇暴队武力镇压集会群众的血腥场面,528这一串平凡的号码,承载了太沉痛的悲情纪实。我们摇动的笔杆,在纸页上洒泪哀号,可是,声息却传不出电脑屏幕那一方寸格子。
静默的气氛,深罩媒体业。528报变过后,中文报业没入垄断、政党控制的漩涡之中,无从跳脱。丧失了竞争环境的中文报,陷入重大新闻不见天日的危机当中。别的新闻不说,中文报业史上最黑暗的一页--“528报殇事件”,竟然只此《东方日报》一家中文报社为文重温,其它主要报社皆静默以对,仿佛五年前的这一天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五年前的这一天,我从“报纸是文化事业”、“新闻是良心工作”的美梦中惊醒,体认到我一直崇尚的媒体事业,不过是套上了文化大衣的服务业;号称“正义至上”的报社,实乃不过逃不脱商业利益考量的商业机构。可是,五年后的今天,我发现还有不少读者迷信报社“以良心办报”,叫人不得不臣服于文字的影响力。
资讯垄断和资讯封闭之所以可怕:惰于思考之外,我们还面对独立思考能力不足的局限,因此,当重复的论调不断复述,而异议长期缺席,久而久之我们便会信以为真。柏拉图说过一个“山洞人”的故事,说几个被捆绑在山洞里的人,长年背对着一团火坐在山壁前,从未看过外面的世界,因此,他们把火光映照在山壁上的影子都错认为实体。在资讯的荒漠中过日子,莫若山洞人坐看火影子。
文学大家鲁迅认为文章可以救国,所以干脆不做医生,跑去做文章。我的医生朋友为摇动笔杆的我感到骄傲。期待哪一天我们摇动的笔杆,可以让我的朋友专心致志地救人;让我们在主流媒体奋斗的朋友们,可以快乐地摇动他们的笔杆、转动他们的长镜头。祈祷528。
(原载《东方日报》生活资讯“晒网打鱼”专栏)
P/S:重点是,《东方日报》一字不漏地刊登全文,没有删去“镇暴队武力镇压集会群众的血腥场面”这一段,很了不起了。你们知道吗,小气鬼《新海峡时报》就删走了Brian Yap专栏文章的这么一段:
"But progress is often faced with resistance from those threatened by change. Increasingly defiant voices against the IPCMC have emerged, even though the violence that broke out at KLCC last Sunday is another drop in the bucket of proof that the commission is more urgent than ever, for both the credibility of the force, as well as the safety of citizens. Its necessity cannot be overemphasised, especially in the face of hostile resistance from some quarters."
详情请参阅Amir Mohammad的blog: http://lastcommunist.blogspot.com/
Saturday, June 03, 2006
露体狂
Thursday, June 01, 2006
Subscribe to:
Commen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