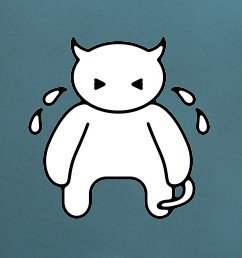在香港和澳门的七天里,我几乎每天都在躲藏,躲到没有爬满蚂蚁的地方去。好像去旅行,就是为了躲藏。
 到港第一天是周末,我决定去听一个声援被捕的中国维权人士许志永的讲座。讲座在旺角的一个二楼书店举行,我独自乘搭地铁,从铜锣湾去到旺角。跟着人群走出地铁站,只感觉人潮从四面八方袭来,我一定是被吓着了,我用了最快的速度,躲入序言书室。
到港第一天是周末,我决定去听一个声援被捕的中国维权人士许志永的讲座。讲座在旺角的一个二楼书店举行,我独自乘搭地铁,从铜锣湾去到旺角。跟着人群走出地铁站,只感觉人潮从四面八方袭来,我一定是被吓着了,我用了最快的速度,躲入序言书室。讲座开始前,我读了数页牛津出版的北岛的新作《午夜之门》,因着还没筹足购兴而没有买下,倒是买了《城市志》的创刊号,创刊号主题正是我所在的旺角。
离开香港之前,我在乐文书室买了北岛的诗集。
这个城市太拥挤,于是我读诗。
诗的构图本身,就是一幅图画。白白的天空下,立着一间间独立的房子,你可以在天空下自由滑翔,亦可在四四方方的房子里自由躲藏。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我在香港特别想要读诗。
到港第二天,我到上环参与声援刘晓波的小型示威,接着回到人满为患的铜锣湾,在崇光百货中在各色名牌货面前游走、困惑、迷失,最终全身而退,退到香港中央图书馆,在空调适度的明亮空间里,看梁秉均的诗。
 其中一首诗,写在70年代。他形容晚上穿行的电车,就像一只深绿色的灯笼,我真喜欢这形容。经他这么一说,铁皮造的电车,一下变温暖起来。这时我脑海浮现的,是龙猫所在的森林里出没的猫巴士。
其中一首诗,写在70年代。他形容晚上穿行的电车,就像一只深绿色的灯笼,我真喜欢这形容。经他这么一说,铁皮造的电车,一下变温暖起来。这时我脑海浮现的,是龙猫所在的森林里出没的猫巴士。去图书馆前的那天中午,我就在上环遇到了几个绿灯笼。它们在街道上自在地滑行,好像懵然不知时光的流逝、景物的更变,走在上环的街道上,感觉好像还可以在哪个转角处遇到张爱玲,或是在哪间茶餐厅见到30岁的也斯。
谢立文在他的最新作品《这是爱》中,把深绿色的电车和咖喱鱼蛋、麻雀仔、白海豚、牛屎花等,形容为“一切美丽光明物”。香港的电车,确是美丽的光明物,尽管香港的景物变了又变、城市的步伐加快了又加快,它们始终维持着尽忠职守而又悠然自得的姿态,在闹市中静静地放光。
生活在那样一个拥挤的城市,就该有着那样的一种姿态。在书店亦被挤到二楼的香港,我始终只是一个过客。胆小如我,只知道躲藏,没有矗立其间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