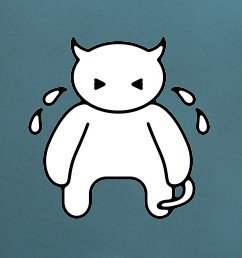Tuesday, May 29, 2007
我吓到你了吗?
昨天遇到老杨,他说我脸清清,问我是不是被人欺负,要我多喝点汤。早前遇到黄文慧,她递给我一罐忘了叫什么名字的药材,给我泡水喝补补身。回家时,伯伯买给我一打鸡精,叫我注意调养身体。于是我明白,我的样子很吓人。我问坐我隔壁的同事,你能接受一夜情吗?别误会,我没有要找猛男进补的意思。
Friday, May 25, 2007
浑人混事
我的部落格是最原始的,没有友情链接、没有会动的公仔,没有会提醒你时间不留人的时钟,没有游客人数显示。不是我不要,而是我不会弄这些东西。我不会,因为我懒惰去学。于是,我部落的款就像白饭捞生抽,只有一粒粒的方块字,偶尔心情好时来点图片作配菜。就这样混着过去,一年余。感谢链接我的朋友没有问我“我链你你怎么不链我?”昨天我在F和Z的协助下,终于为羊人部落加了一点小功能。2007年5月24日过后的第一天有66个朋友来这里玩。还有,Z帮我加入了“独立广告联盟”,在这里贴了两个广告。据说,有人点击一下那个康仔&燕婷的结婚广告,我就净赚三分钱;有人从青色的广告那里买一本“独立购”的书,我就赚90仙。没什么,只是为昨天留一个记录。
Thursday, May 24, 2007
访问
我跟各种各样的人做过访问。跟政治人物、雕刻艺人、影星、歌星、大导演、评论人、科学家、作画的、写作的、画漫画的、写诗的、做食物的、设计衣服的、耍杂技的、做生意的,各种各样。
他们之中,有的你还没访问前很想见一见,有的从来就没想过要见面,有的甚至你抗拒见面。可是最终你都见到了他们。想要接触的人之中,有的成了我的朋友;有的,见与不见没什么差别;有的,见了之后希望自己从未见过他们。可是,时间是径直飞行的,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接触自己想要接触的人是我当记者的动机之一,可是这个诱饵吊起来的惊喜和失望,称起来是重量相当的。通常一个人之所以会成为采访对象,要嘛他掌握一些特殊的资讯,要嘛他有一定的才能或才华。你选择专访他,他自有他独到之处,最后为他加分或减分的,是他的谈吐和品格。
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它可以长得让你如坐针毡,最后落荒而逃,也可以短得让你感叹时间匆匆,不及饱赏冰山全貌。匆匆一会之后,评论的继续评论,写诗的继续写诗,拍片的继续拍片,可是,这个人从此在另一个心目中留下印迹,或好,或坏。
他们之中,有的你还没访问前很想见一见,有的从来就没想过要见面,有的甚至你抗拒见面。可是最终你都见到了他们。想要接触的人之中,有的成了我的朋友;有的,见与不见没什么差别;有的,见了之后希望自己从未见过他们。可是,时间是径直飞行的,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接触自己想要接触的人是我当记者的动机之一,可是这个诱饵吊起来的惊喜和失望,称起来是重量相当的。通常一个人之所以会成为采访对象,要嘛他掌握一些特殊的资讯,要嘛他有一定的才能或才华。你选择专访他,他自有他独到之处,最后为他加分或减分的,是他的谈吐和品格。
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它可以长得让你如坐针毡,最后落荒而逃,也可以短得让你感叹时间匆匆,不及饱赏冰山全貌。匆匆一会之后,评论的继续评论,写诗的继续写诗,拍片的继续拍片,可是,这个人从此在另一个心目中留下印迹,或好,或坏。
Saturday, May 19, 2007
My Fair Lady
我看过一些歌剧,可我真的不懂歌剧有什么好看。如果不是因为350元的免费票,兼星期五无所事事意志消沉,我想我也不会巴巴地跑去看什么歌剧。我们两个穿牛仔裤进场,穿梭在衣香鬓影之间,活像两个外星人。排队进场时被挡在一幅裸露的背部后面,我看着女背上一粒粒的豆豆印,心里想着人们花几百块钱买票看歌剧的理由。后来我看见活像金龟的男士,还有以《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女婢造型出现的玉女,渐渐地有些明白。
Thursday, May 17, 2007
遇见李康生
两只耳朵,在公寓
凌晨三点了,楼上的房客仍旧大呼小叫,在更靠近耳边的地方,一把似念经似念新闻的声音在空气中潜行。我醒着,不知是这些声音吵醒了我,还是因为自己醒着,所以听见了这许多声音。
生活了28年,这是我第一次住进公寓。公寓大概是“公共寓所”的简称吧。这类寓所像高高的蛋糕,被切割成一块块,几个人分得一块。我安家的这块蛋糕高六层,我分得的这一块在二楼。蛋糕兀自矗立,没有保安人员看管,有种风烛残年的味道。不知是这个蛋糕够旧够市井,还是纯粹因为保安不严闲人任进,听说这里常成为独立电影的场景。
住公寓跟住平房自然有很大差别了。住平房只有左邻右舍,住公寓则上下左右都有陌生人,上下左右的异动都会钻入耳髓。就说那一天吧,我在房里看书发呆,突然传来一声炒锅的响声,然后是一把尖尖的女声。我以为什么人炒菜时烫伤手,不以为意,后来才知道是隔壁家的女房客拎着新买的炒锅从外头回来时在楼下遇上了攫夺匪,炒锅脱手,叫声跟着脱口。
大部份时候我无法为声音溯源。我听着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声音,度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在晚间的过路人眼中,我不过是作为一盏未熄的灯存在着。路过别的蛋糕时,别人在于我,也是一盏可有可无的灯。公寓,它让人变得渺小,或谦卑。
生活了28年,这是我第一次住进公寓。公寓大概是“公共寓所”的简称吧。这类寓所像高高的蛋糕,被切割成一块块,几个人分得一块。我安家的这块蛋糕高六层,我分得的这一块在二楼。蛋糕兀自矗立,没有保安人员看管,有种风烛残年的味道。不知是这个蛋糕够旧够市井,还是纯粹因为保安不严闲人任进,听说这里常成为独立电影的场景。
住公寓跟住平房自然有很大差别了。住平房只有左邻右舍,住公寓则上下左右都有陌生人,上下左右的异动都会钻入耳髓。就说那一天吧,我在房里看书发呆,突然传来一声炒锅的响声,然后是一把尖尖的女声。我以为什么人炒菜时烫伤手,不以为意,后来才知道是隔壁家的女房客拎着新买的炒锅从外头回来时在楼下遇上了攫夺匪,炒锅脱手,叫声跟着脱口。
大部份时候我无法为声音溯源。我听着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声音,度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在晚间的过路人眼中,我不过是作为一盏未熄的灯存在着。路过别的蛋糕时,别人在于我,也是一盏可有可无的灯。公寓,它让人变得渺小,或谦卑。
Monday, May 14, 2007
为什么冬菇要配鸡脚?
那天我们去吃云吞面。我叫了一个冬菇鸡脚云吞面。
同事问:“为什么冬菇一定要配鸡脚呢?”
我说:“因为如果鸡脚没放冬菇就没有冬菇味了。”
同事说:“那冬菇没放鸡脚就没有鸡脚味了。”
是,这是很重要的发现。延伸下去,如果张爱玲没有配胡兰成,她就没有胡兰成的味道了;如果徐志摩没有配陆小曼,他就没有陆小曼的味道了;如果陈阿始没有配独立新闻在线,她就没有独立的味道了。这道理最简单不过了。
同事问:“为什么冬菇一定要配鸡脚呢?”
我说:“因为如果鸡脚没放冬菇就没有冬菇味了。”
同事说:“那冬菇没放鸡脚就没有鸡脚味了。”
是,这是很重要的发现。延伸下去,如果张爱玲没有配胡兰成,她就没有胡兰成的味道了;如果徐志摩没有配陆小曼,他就没有陆小曼的味道了;如果陈阿始没有配独立新闻在线,她就没有独立的味道了。这道理最简单不过了。
Thursday, May 10, 2007
新住客
Wednesday, May 09, 2007
依约的碎片
 我去依约住了几天,喝了依约安娣煮的班旦叶水、依约安娣煲的玉蜀黍,还打破依约安娣的一个杯子。心被碎裂的玻璃划伤了,离开时依约成了伤心地。
我去依约住了几天,喝了依约安娣煮的班旦叶水、依约安娣煲的玉蜀黍,还打破依约安娣的一个杯子。心被碎裂的玻璃划伤了,离开时依约成了伤心地。去时我们找到了油棕园里的叫化鸡,看人剥开干泥巴,取出热腾腾的鸡只。叫化鸡上桌时,四双筷子和汤匙们快乐地飞舞。喝了椰花酒的脸,咚咚咚地红了起来。我们举杯,预祝民主胜利,那真是一个快乐的晚上。
后来我们住进了安娣的家。安娣有一个干净安静的家,安娣也有平易近人的个性,我喜欢安娣和她的家。我认床,通常外宿都难以入眠,可是安娣的家不一样。一天早上菲见我睡得直挺挺的没有声息,还以为我睡死了去。
在东奔西跑、南征北伐的日子里,早上的两粒半生熟蛋和晚上的睡眠是一天最美好的开始和结束。开始和结束之间,充斥了语言暴力、行为暴力,有钱有势的一方,成了主宰真理的一方。许多不合理的事情被合理化,我无力阻挡,只能挥笔记录。在强权面前,捉笔的人是渺小的。
那一天,我吃安娣煮的玉蜀黍和班旦叶水当午餐。一个不小心,杯子从桌上掉落,玻璃碎了一地。于是,依约之行最后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画面。我一路听着U2的呐喊一边诅咒猛烈的阳光,恍恍惚惚地回到城市。
Monday, May 07, 2007
给她一分钟
保障女人的安全不是男人的义务,许多男人生来也没有保护女人的天份,但是在吉隆坡这个罪案率偏高的城市,学习在危机潜伏时照顾身边的女性朋友,对稍微有风度和思考能力的男性应该不算太苛刻的要求吧。
送女生回家时,确保女生安全进入家门才离开,是基本的风度(至少我和我的女性朋友和一些男性朋友都会这么认为),可是偏偏有一种男生,把你送到家门后即绝尘而去,任你在危机四伏的境地中拧开栏栅的锁头。
开锁的一分钟时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她可能会被攫夺匪钉上、被色魔看中,第二天登上报章头条。如果你愿意多花一分钟时间看她进入家门后才离开,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纵然她不是你女朋友,没有权利要求你关心她的安危,但是身为朋友的你,难道就没有想过要耗那一分钟的时间去确保她的安全吗?
我遇过把我扔在家门前的男性朋友。想起都会不寒而栗。我也遇过过度关心的男性朋友,他看我入门后还会怀疑自己的眼睛,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已经安全进门。你不必细心到这个地步,但至少,给她那区区一分钟的时间。
别低估那一分钟在女人心目中的位置。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和一个对她有好感的男人约会,他看来一切都好,只是送她回到家门后即绝尘而去。那一刻,她对他的所有幻想宣告破灭。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送女生回家时,确保女生安全进入家门才离开,是基本的风度(至少我和我的女性朋友和一些男性朋友都会这么认为),可是偏偏有一种男生,把你送到家门后即绝尘而去,任你在危机四伏的境地中拧开栏栅的锁头。
开锁的一分钟时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她可能会被攫夺匪钉上、被色魔看中,第二天登上报章头条。如果你愿意多花一分钟时间看她进入家门后才离开,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纵然她不是你女朋友,没有权利要求你关心她的安危,但是身为朋友的你,难道就没有想过要耗那一分钟的时间去确保她的安全吗?
我遇过把我扔在家门前的男性朋友。想起都会不寒而栗。我也遇过过度关心的男性朋友,他看我入门后还会怀疑自己的眼睛,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已经安全进门。你不必细心到这个地步,但至少,给她那区区一分钟的时间。
别低估那一分钟在女人心目中的位置。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和一个对她有好感的男人约会,他看来一切都好,只是送她回到家门后即绝尘而去。那一刻,她对他的所有幻想宣告破灭。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Saturday, May 05, 2007
Tuesday, May 01, 2007
不答
渐渐地,他们都不论政了。记者会上,记者问了较为刁难的问题,他们总是脸色一沉。话毋须说出口,谁都知道这名记者问了不该问的问题。被问题绊倒时,装傻扮懵一类干脆挥一挥手似愠非愠地说:“哎哟,你别问这样的问题了。”随之把头转向另一名记者,任由问题吊悬半空。
有的人甚至在问题抛到面前后,假装赶场,趁乱兀自走开去,任发问的记者愣在当地。也有的,敷衍了事、神志散漫地回答了你的问题之后,悄悄吩咐熟络的大报记者莫在该问题上着墨。还有的,直截了当地说:“今天的活动是环保,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你不觉得环保很重要吗?”
政治人物专拣轻松的议论,同样渴望轻松完工的记者投其所好。渐渐地,越来越少记者敢逼政治人物论政了。记者先生小姐们说,这种问题还是不问为妙;这种问题,还是等别人来问吧。他们也说,这种问题,问了都是不能写的啦,我问来干嘛?
于是,政治人物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轻松自在。他们四处露面、开幕、宣布拨款、捐钱做善事,在农历新年、卫塞节到佛堂浴佛、在国庆日时发表一下爱国的伟论、在补选时到选区唱唱卡拉OK,温厚爱民的形象即轰然而立。
“只要不说话,就不会说错话,不论政担保万无一失,论政这事还是能免则免。”我不聪明也不算太笨,如果我是政治人物,在这样一个国民无甚要求的国度,我会作此想。最悲哀的是,我想到的,他们怎么会想不到?
有的人甚至在问题抛到面前后,假装赶场,趁乱兀自走开去,任发问的记者愣在当地。也有的,敷衍了事、神志散漫地回答了你的问题之后,悄悄吩咐熟络的大报记者莫在该问题上着墨。还有的,直截了当地说:“今天的活动是环保,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你不觉得环保很重要吗?”
政治人物专拣轻松的议论,同样渴望轻松完工的记者投其所好。渐渐地,越来越少记者敢逼政治人物论政了。记者先生小姐们说,这种问题还是不问为妙;这种问题,还是等别人来问吧。他们也说,这种问题,问了都是不能写的啦,我问来干嘛?
于是,政治人物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轻松自在。他们四处露面、开幕、宣布拨款、捐钱做善事,在农历新年、卫塞节到佛堂浴佛、在国庆日时发表一下爱国的伟论、在补选时到选区唱唱卡拉OK,温厚爱民的形象即轰然而立。
“只要不说话,就不会说错话,不论政担保万无一失,论政这事还是能免则免。”我不聪明也不算太笨,如果我是政治人物,在这样一个国民无甚要求的国度,我会作此想。最悲哀的是,我想到的,他们怎么会想不到?
Subscribe to:
Commen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