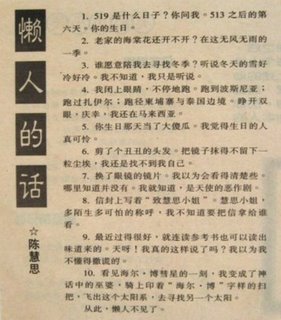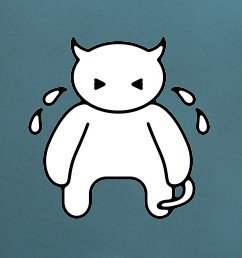雨多了,转眼竟就到了年尾。29岁的人快变30岁,39岁的人再多一个月就是40岁了。一开始我们都是一年又一年地过,转眼就是十年十年地过了。去年7月开始当新闻记者,一年以后惊觉“周期”的存在:八月是马华公会和民政党的代表大会;十一月是巫统代表大会。如果我年复一年地当新闻记者,这些日子每年都会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周而复始的赶场式生活,我无法想象,以致拒绝想象。
比起一个天天得问乘客“要咖啡还是要茶”的空姐,记者的工作天天都一部电影。每一天,我们都有不同的内容。我们见各色各样的人,我们听林林总总的话,我们走向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们每一天,都必须活在警觉的状态中,每一天,都期待自己写出惊天动地力撼山河的文章。我们活在时针和分针的尖角上,警觉地观测着世态的变化,可是也许正因为我们伏在时间的尖角上,我们感受不到时间它在我们身边流过。总是如此,一晃头,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晃头,一个月过去了;当雨季重临,水灾的气味越来越浓洌,我们才突然惊觉:天呀,又一年了。
就这样,又一年。我无比焦虑。今年的我比去年的我进步了吗?长多一点智慧了吗?活得有意义一点了吗?我一点信心也没有。糟糕的是,我发现我电影的内容在重复当中。一批人的家园被无情的大铲摧毁,又一批人的家园被无情的大铲摧毁。巫统代表大会又来了,巫统代表大会又走了。种族主义的言论沉寂一年之后死灰复燃。在野党和公民团体再也喊不出什么新意。我是在前进中还是在原地踏步?我真的活过另一个年头了吗?我在时钟当中打圈徘徊,焦虑无比。
我需要时间好好思考,可是时间却不会因为我顿脚耍脾气而停步让我仔细思考。在我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秒针已经走了一圈又一圈。2006年,我蹉跎了你了吗?我要怎样活出不一样的2007年?我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焦虑。我老了,耗不起时间重复同样的生命内容。怎么办才好?我与生命开始展开赤裸裸的长时间对谈。而时间,它流过。